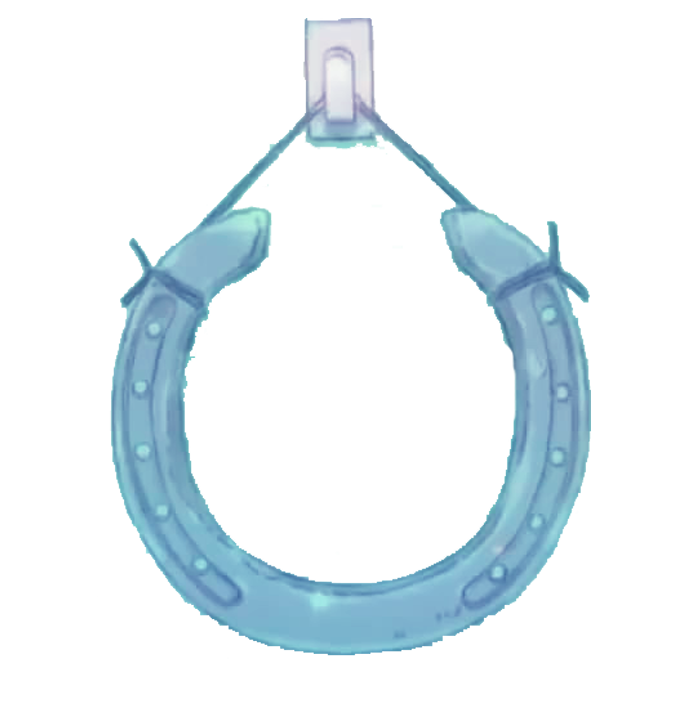我心浑沌 ——《应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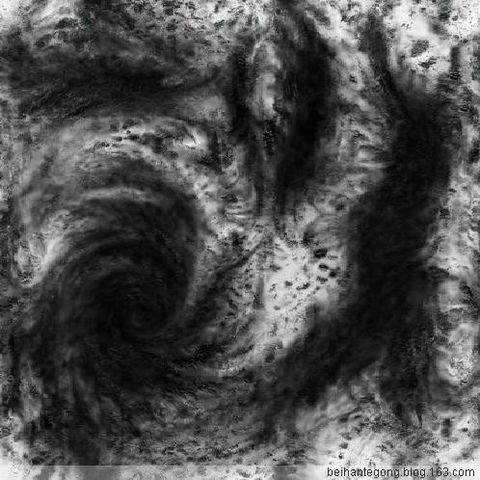
终于到了最后一篇了,根据长短交替的顺序,这篇算是短的,在《大宗师》中用了大量篇幅谈了“道”与“真人”后,以谈偏世俗得为政之道似乎有点狗尾续貂。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应帝王》一方面是谈无为地治理,另一方面其实还是有针对每个人自身的意思。王博的《庄子哲学》中说,这里的“帝王”可以看作是理想的统治者,也可以理解为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帝王”。虽然这样难免会被诟病牵强,但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在《庄子》内七篇探讨个人心灵生活的大背景下,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既然提到了“帝王”,还是先来说说为政之法吧。《应帝王》中重要的是一点是“避免强加意志”,道家是反法家用法律制度来强制规范民众的,文中言鸟虫尚且会趋利避害,人当然也会尽可能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去做。认识到这点是十分重要的,这里又要提到此前我提及的一些学派认为人有原初的道德冲动,可以勉强归为性善论(说“勉强”的原因是我不希望归为一种论调),我当时的观点是光靠这种有些虚无缥缈的道德冲动是不靠谱的,那法家的法律制度呢?其实原来我还是有点倾向于依法治理,先制定社会的一般准则,再努力去实践它们。但庄子在这里或许反对的是一种过重的刑法(让许多人罹受残疾),或者他连一般的法律的约束力也不相信,这么想当然也情有可原,毕竟法律总有空子让人去钻营取巧。
而庄子提到的“无为之治”又该如何评价呢?“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这可能接近于我本身理解的“无为”,顺其自然。但这样似乎又回到了“原初道德冲动”使天下治的感觉,或者是民众没有约束而自由散漫,似乎都与“治”不符。当然我觉得这种对“无为”的理解是不恰当的,我觉得就全篇行文而言,“无为”的一方面似乎可以用“不强加意志”(和“无容私”可能相近)来解释。不强加意志的问题我记得在最早写的一篇《齐物论》中提过,当时是因为一个有关尧的一个寓言,尧同样是一个统治者,他“希望”某些人也能被“解放”,于是去攻打它们(仅凭记忆,意义可能有些失真),这便是“有为”,将自己认为“好”的施予别人。其实法律制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有为”,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人们都需要按照法律去行动,否则便会受到惩罚。
那么“不强加意志”是怎么样呢?便是“功盖天下而似不在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统治者隐藏了,而天下得“治”。但这里其实又引发了一个小问题,“似不在己”其实隐含着“功本在己”,也就是说,统治者并非什么都没有做,他其实做了,只是民众没有发现,因为他做的事被民众看成是自己做的了。这就有点意思了,此前有些人多次和我谈意识形态控制与限制自由意志的问题,我的观点是让民众意识到自己遭受控制(如《1984》)的政治是需要被否定的,而且民众应该反抗这种控制。而那种民众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受到控制的统治呢?达成这种统治的途径可以有《1984》中的“新话”语言控制,可以是通过高效的政治课(不是现在这种)进行意识形态熏陶,或者是通过文化环境中的文艺作品进行不自觉的引导。这种统治似乎和刚才提到的“功盖天下而似不在己”有点像了。但是总让人觉得有点别扭,感觉一种贬义的东西忽然成了褒义。在我看来这倒本来便是中性的,毕竟我们平时读书看电影,其实也是会被无意识地引导(我觉得即使主动地抵制也无法做到完全避免引导,或者说有些我们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反而会让我们主动被引导)。至于为什么被看为贬义,其实是我们跳出了那个统治环境,从第三方的视角看到了“功本在己”,所以就如民众意识到自己被统治的情形一般,会有一种反抗它的冲动,而对于正在被统治的民众,实际上他们或许正处于“化贷万物而民弗恃”的状态。至于我所言的这种统治与庄子的“无为而治”是否契合,以及这种统治的最终应该被肯定还是否定,其实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毕竟还是需要进一步地了解。
其实谈了那么多统治的问题,在《应帝王》中都不是重点,有人问无名人“请问为天下”的时候,其实最初的回答是“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庄子其实是有些看不起谈为政之道的,或者说,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去谈,那边是对个人心灵的态度。谈为政之道只是希望理想的君主能够不对自己“强加意志”,让这“人间世”的艰难少一些罢了。
这一篇的开头其实呼应了《齐物论》中的“啮缺四问王倪”,当时是说不知万物有共同标准、不知自己不明白什么、不知万物是否能够被知道,甚至连自己的“知”是“知”还是“不知”都不知道。这一方面是不自我夸耀的表现(啮缺在开头可是欢呼雀跃,对比立显),另一方面是这些东西是否知晓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对自己“知”的本身的质疑。我有那么多知识,我就一定知道它们吗?或许我们都还只是处于一个“无知”的状态。“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这句话中的“应”即“应帝王”的应,有顺应的意思,于是“应帝王”也可以理解为顺应自然而成为自己的帝王。把心比作镜子的比喻,其实此前多次提到过,镜中本没有物,有了世界才有了镜像,而世界变动,镜中之物也随之变动,这似乎有种“不藏”之意,但镜子是不变的,这便是“不将不迎”了。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拥有固定的知识实际上还是“无知”,可能正因如此,才需要“弃知”吧(从第三篇开始讨论的问题似乎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应对这个变化的世界,可能需要一种“浑沌”的心态吧。
为什么提到浑沌,其实是因为《应帝王》篇末,也是《庄子》内七篇的结尾,提到了一个令人感到说不出的忧伤的寓言: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浑沌是庄子(或者我理解的庄子)所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而“倏”与“忽”“出于好心”便把自己的意志加于其上,凿出七窍,化而为人,投身于困厄的“人间世”。“浑沌”死了,而我们所追求的心灵自由呢?
2016.5.12 《庄子》内七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