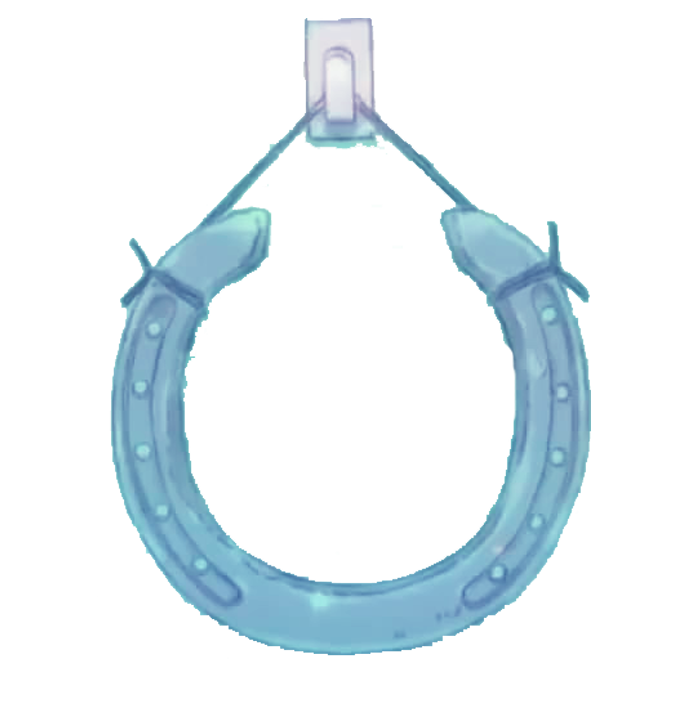与尼采短暂重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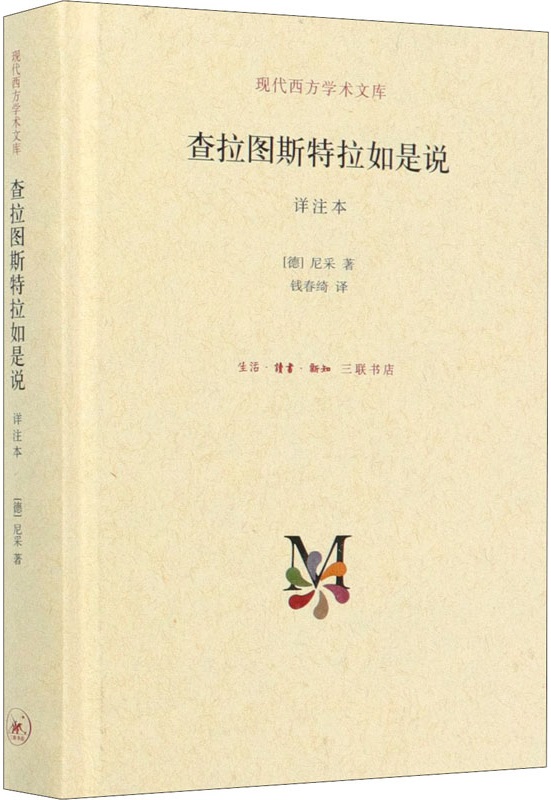
令人意外的是我曾经没有写过关于尼采的闲想,明明他的许多(或许被转述和改造的)想法是我进入哲学的最初动力之一。此次本来也想从尼采发疯前不久写就的自传《瞧!这个人》切入,按顺序阅读他的作品的,但在看完《悲剧的诞生》后,觉得他关注的破除旧道德这个点,如今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探讨重点,所以便直接进入他最重要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了,不过即使是这本书,其实我也只是略读罢了,习惯了其他哲学家条理式的写作,一下子进入这诗化和隐喻的作品中还是招架不住。当然我也打算只是略作了解,将其当做一个背景材料,重点看后人对此如何评说。
曾经听闻尼采的酒神精神、强力意志、超人、永恒轮回等概念,深深着迷,甚至把他的发疯都看作某种象征意味的事,可以说我自称半个存在主义者的源头便是尼采。如今在哲学史的背景下再度切入,自己也随着个人的成长经历、体验、思考了更多,感觉更为冷静地看待尼采了。我想尼采的自传中对自己的评价十分到位,他是炸药。在我需要与外界的束缚做斗争时,这炸药能为我开路,肆意的重估外部世界所谓的“道德”。如今我自感到已没有外界的强制性束缚,所面对的更多的是潜移默化或者软化的束缚,确切地说,我有选择的权利,而我的选择是我受到束缚的原因,我对束缚的抗争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的抗争,这时若是运用炸药,便可能会炸伤自己了。我需要另一种平稳但依旧有突破和创造性的方式去应对我的生活。
早先一段时间和某位朋友聊起这本书时,他提到书中骆驼、狮子、孩子的精神三阶段,当时便觉得深以为然,或者说早已内化到我的想法当中去了。骆驼指的是背负外在的责任,狮子指的是从“你应当”变成“我想要”,而孩子确是肆意随心,遗忘此前精神上的这种斗争。听某个讲座 中的观点,尼采本人还只是到狮子这个阶段。阅读他的作品确实也给我这种感受,尼采的文字中蕴含着强烈的对抗性,与世俗的旧道德、庸俗的盲信者势不两立。由于我是从哲学史切入,所以对这种趋势反而能够体会,彼时上帝的神圣性在人们心中渐渐淡去,而宗教和延伸的道德却依旧掌握着话语权,即使是康德费希特这些哲学家,也必须在著作中拟造一个道德的上帝,否则便会被指责为无神论者。尼采面对的是那样一个压抑的道德环境,文字上过火一点十分能让人理解,就如上世纪的鲁迅也写下“满书是吃人”这样的观点,也不妨碍我们如今再度发掘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思想。
如上文所言,对我个人而言,这一抗争的过程已经大部分过去。所谓的抗争,面向的对象是中小学时代、甚至大学时代的外部教导或者强制性的要求,当时在外部的限制中和内在的心灵张力中寻求一个合适的平衡,算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我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尝试摸清限制的边界,然后抓住边界未约束到的部分施展,直到这一空白处也被砌上墙,再去寻另一处。我希望我所做的都是字面意义上“不越轨的”,但有时最大程度满足我的心灵需求的。这当然也不能算是长久之计,但毕竟陪伴我度过了年少的时光。大学时期算是部分逃出牢笼,博士时期则更为彻底,我获得了许多自由,限制的边界也大大后退,而转变为某种选择带来的“不得不”,这点或许在下文可以再详细展看。所以在我心目中,往日我是在骆驼和狮子之间进行转变,而现今则在狮子和孩子的精神状态之间。至于以往的旧道德,原先它贴在我脸上让我需要应对,而如今我可以把它们扫进一个角落,不必管它们。至于宗教,也是从不了解时的好奇,到如今看待为一种文化的理解,再到此后了解透彻后的抛弃。我曾由于康德还引入道德性的上帝而有些精神洁癖的感觉不适,如今也觉得不过如此,只要这种要求不要普适到我身上即可。我觉得,无视是比蔑视、仇恨、对抗等态度更加彻底的一种结束,无视说明我如今并不需要在意相关的问题,其间的纠结也早已被彻底地解决,所以我也便没有特别的兴趣去阅读尼采更多关于批判旧道德的著作了,当然那里面还是有很多金句的,什么“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你”,“不曾把你打败地会使你更强”,“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等等,我都是深以为然但也不再会着重讨论吧,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已经是定论、我日常所做的事罢了。
虽说不着重讨论,还是来多说几句吧。两年前的独居让我对自己的状态时刻保持关注,甚至回看时还有些担忧,如今这种关注和担忧其实也在持续,但当我细细比较,发现也已大不一样,如今的我每天自然而然会做许多“有意义的事”,如哲学阅读、静观思考、听讲座等,而我的忧虑实际上也是在这基础之上,即在过去的我眼中看来,如今的生活状态实际上能算是“每日起舞、不曾辜负”,而我则是在这一基础上依旧追寻更()的道路。这里的括号里我应该填什么呢?或许来转入对强力意志的讨论吧。
在讨论之前,先插叙一段轶事。尼采曾阅读叔本华的著作,深以为然。但在这本书中(以及其他作品中)对叔本华进行了超越。他认为叔本华关注的是意志要保全自己,而他觉得如没有存在便没有意志,保存也就无穷谈起,所以生存着的意志本身无需考虑生存的问题。这当然有点文字游戏,但对叔本华的态度确实和我比较一致,意志中的核心不是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不受损害,而是要尽可能地展现、绽放(我接受的是《存在与时间》中绽出的想法)。所谓的强力意志,也便是这种态度,不断地超越自己,达到所谓超人的境界。但正如尼采要超越叔本华,如今的我也选择进一步超越尼采。他认为人并不是目的,而只是猴子到超人之间的桥梁。这点上我反倒认同康德(虽然我和康德的着重点其实不一样),认为人就是最终目的。尼采追求超人的态度,确实很容易被误解成替代上帝的另一个“上帝”,或者以人之位去取代上帝之位,尼采自己有所澄清,但无可辩驳地是他依旧对当下的状态采取了某种否定的态度。与我而言,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是值得过的,我在始终突破自我,并不代表这个被突破的自我便是无意义的。偷一句尼采自己的话,没有梯子,还怎么爬到自己的头上呢?其实尼采更多的阐述了人要成为超人的趋向,而没有详述成为超人的过程,他只说越过自己的心,却没有说如何越过。否定当下,才更有趋向去接受一种永恒轮回的时间观。
对永恒轮回的解读当然可以有多种,我还是从多角度尝试一下吧。首先由于往前时间无限往后时间无限,推导出当下(以及整个人生)会不断重现,这个推导当然是不成立的,就如同看到一个无限不循环的Pi便觉得Pi里包含着所有的奥秘一样,无限也可以与无限不同,无限也不一定能包含无限。道教里是用这种无限否定当下一世的意义,所以要追求炼丹长生。尼采则是相信无限会带来循环,一遍遍地重现让当下这一刻也有了意义(当然为啥有意义我也不太能体会)。另一个切入点是,认同当下的生活,即使它会一遍遍重现,也坚定地走下去。这种当然是在永恒轮回下也肯定当下的意义,但在我看来有些没必要,当下即是当下,此时的所感,即使再度被重复,下一次重复如果无法影响到上一次,那对此的谈论本身反而失去了意义。当下的意义不必由未来肯定,当下自身包含着意义。在此当然可以再提一句西西弗斯,虽然得知石头每次都会再滚下来,但这一回向上推的过程,如果扩展到人生这一整个长的时段,实际上就其自身便值得经历了。或许在石头即将落下前,人会变得意志不坚定,突然感觉一切皆成空,人生又得重来,但至少在那之前,在意志还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向上的过程中,可以用这种当下的意义让人生的旅途变得幸福。总而言之,我对尼采永恒轮回的观点是不甚关心的,因其假设层面便不太牢靠,承认假设也并不能推导出什么更令人认可的事物,那何必要采取这一假设呢?
这一点和当时我对待康德“道德上的上帝”的态度类似,康德认为上帝存在或不存在都不可证,但可以由信念保证一个道德的上帝来实现善良与幸福的合一以至于至善。而我则是既觉得上帝的这一假设无必要,也无需实现善良与幸福的合一。当时似乎留了一个尾巴,来看尼采是如何超越这一态度的。在尼采这里,似乎善良联系着旧道德,早就被批驳地一无是处了,而幸福也不是他追寻的目标,从查拉图斯特拉来到幸福岛而又离开回到自己的山洞便能看出。所以这一层面上,尼采和我选择相近但略有不同。此前对叔本华作品的讨论 中,我说叔本华早把幸福的秘诀告诉我们了,就是让从愿望到满足这一过程保持一个合适的节奏,这点基本成为我未来一段时间的幸福观了。至于善良,目前我的态度则更倾向于上文提到的“不越界”、“在限制中寻求张力”。偷一手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然后提一句,尼采也提到了对待过去,说“过去是”是意志的切齿痛恨和最寂寞的悲哀。但此后也说了超越这种想法的途径,却在提到追求强力意志时戛然而止。如何与过去和解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话题,我此前有几篇文章的核心便是处理这个问题。但随着时间的前进,“过去”的范围也不断地在变大,我能在当时处理几年前的过去,而当下在下一刻也立马成为过去,未来某一时间或许也需要去处理。所以这个问题或许无法一劳永逸,正如意志不断超越自己,过去也在不断地堆叠加厚。对这个话题或许我在阅读完《存在与时间》后会有更完善地解答,因为在我看来尼采好像没太说明白(或者我没太看仔细和看明白)。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者的互动,实际上正也是我之存在与我之时间互动的核心体现。
接着,我想讨论一个曾经被思考地很深入,但如今却需要再度审视的话题,即孤独。孤独和孤单(孤零零)的区分在这本书里有着重讨论,这个名词辨析也早已内化于我,我便不再展开。我想谈的是孤独自身。引起我注意的是第二部初的一句话:“我皈依孤独已经太久了:因此我忘掉了缄默”。由于理解力所限,我就从字面和上下文意思来理解(还有查拉图斯特拉返回山洞那一段也有再次提到),这里体现尼采希望将他在孤独中的所得分享给世人,而后文还乡时则是意识到在众人之中反而由于不得理解而感到孤零零。这里或许书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和书外的尼采产生了一些偏离,在书中,查拉图斯特拉最终回到自己的山洞,独自体会永恒轮回带来的生命意义,可以说似乎已经学会了缄默,而实际生活中的尼采,在这本书后依旧写作与表达,直到发疯前写自传时还渴望通过区别自己于他人的方式来表达和获取理解。尼采心目中的至高或许像正午的太阳,沉默着为世间万物带来温暖,不需要世人的膜拜或理解,也毫不在意。尼采想做太阳,但他不是。这一点,当我得知尼采发疯前十年里保守病痛折磨时,更为深信。虽然尼采可以以他的思想超脱身体上的病弱,但在此基础上或许更多的是接受他人的帮助,而无法奉献于他人。在这里我忽然联想到《浮士德》的最后,浮士德沉湎于水坝的即将建成说出那句“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虽然我刚查了一下好像是他把鬼怪在挖墓道当成在造大坝了),这里的落脚点还是奉献的而不是为己的。
拉回来一点,这里我想探讨的是,因孤独有所得而“变成奔腾而下的溪流”,和因不受众人理解而选择缄默,两者何者是我所取的?以往的我会选择后者,但如今看来当时只是查拉图斯特拉上山修道前。这个孤独与缄默是在他修道十年,下山传道而再度上山、决定要再度下山时的抉择,所以或许当下的我才不过是处于第一次下山传道的时刻,连这个抉择的时刻都还没到呢。不过我问出这个话,其实是对近两年来,由于曾经的孤独终于能在某些场合得到释放而忘掉缄默的一次反观。可以说,曾经提起的“指向自己”某种意义上便是承认彻底堕入孤独,而近来对此观点的拒斥与调和,则是我对孤独的一次背叛。我仿佛在与挚友的关系间得到了慰藉,仿佛与挚友的交流能让我克服孤独。当然其实我也知道,克服必然是做不到的,而且容易导致更深刻的孤独(加上孤单的孤独),这是以往的经验的结论。所以如今的交流或许是某种孤独的缓解,或者说终于有人能够部分懂我心的释然,即使一个人无法完全读懂我的心,我所有的挚友加起来是否能够让我心中的一部分得到承载呢?我又时刻警惕着言不及义带来的麻痹,让谈话尽可能地直接指向孤独,但实际上我心中感到,孤独的结构实在有些复杂,我近来成功的一些尝试也不过是拨开了以往多次尝试而无果的表层,显露出来的反而是某种更深意义上的孤独。
目前我把期望寄托在《存在与时间》之上,我曾读过它的前半本,便已被“沉沦的必然性”当头一棒。哲学史中提及了后半本的结构,但最终的探索还需要我自己去完成。或许答案正藏在我未读的后半本里的“向死而在”,或许藏在读后半本时的所思所想,或许我在读完之后依旧未得真解,而再去尝试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不过在孤独这一点上,我想尼采或许不能帮我什么了。参考他本人的经历,与叔本华神交而后超越,对瓦格纳的崇敬和友谊则在此后破裂,与莎乐美的所谓友情或爱情无疾而终,虽然她曾为尼采带来了向上的生命意志。在尼采的世界里,曾有过友谊带来的欣然,但在这本书中(体现他后期思想)则更多地表现他孤独的心境。对我而言,我的未来依旧值得探索,或许二十年后我才能更加贴近尼采在写下这本书的心境。我经历过冲突,但我不曾经历严格意义上的决裂,我的个人经历让我在与人交流这件事上,虽以悲观为主,但仍包含着一线希望。
在此忽然想质问自己,究竟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或者偏好如何?就我对自己的观察,我往往做着“最坏”的打算,却又想着最坏也不过如此,反而由此生发出乐观与自信了。截止当下,现实确实没有超出我所想的最坏,所以一切向好。至于超越我所想的最坏是否会发生,我不知道,而且这甚至比我的必然死亡这件事的确定性还要模糊,所以我不妨便先当它不存在,等真的发生了再做考虑吧。我可以为可预期的变数做出准备,对不可预期的变数,便顺其自然吧。
19:01 2022/5/29
告别尼采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