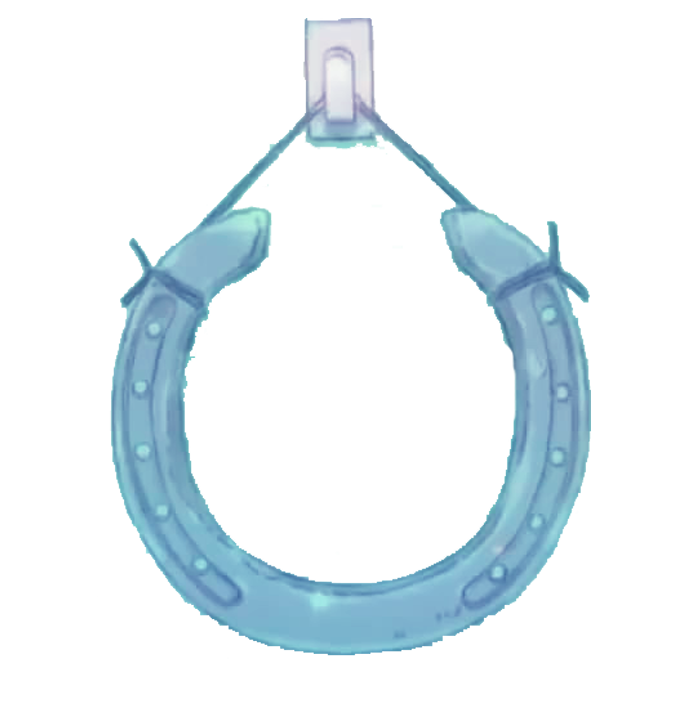时间与焦虑
由于英国学期很短,一转眼又到了最后一周了,然后便会有长达半年的假期。虽然对博士而言假期和学期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我也会把学期结束作为一个时间点来看待。两周后便是半年整,博士生活将会过去六分之一。而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近几日的心情日记始终低位运行,它作为个人状态的间接反映,如果始终表现糟糕,那么我需要做些什么去改善的。换个角度而言,心情日记是一种预警系统,而写作或者思考是解除警报的较好方式。
此次的标题依旧是“时间与XX”,因为我觉得博士期间讨论的话题避不开几个重要前提:博士期间绝对时间是有限的(若干年);博士期间相对可用时间是大量的(95%);博士期间的时间是需要被合理利用的。许多讨论只有在这个环境下才有意义。
上次的切入点是快乐,而这次则是不快乐。即心情日记的加分项和减分项。前者用做事和对这件事的自我感觉可以简单量化和相加,而后者则是一种综合的感觉,时常以“天”或者睡醒到再次睡觉的这个区间为单位,所以更难量化。此前提及“疲惫感”和“负罪感”,也都是一种模糊的量化,往往是通过最终心情结果减去快乐的事的加成得到的差值。这一次我也不希望将其量化,而是希望探究其组成模式。
首先可以简单地将其分为身体的和心理的,“疲惫感”属于前者,“负罪感”属于后者。这两种感觉显然无法囊括所有的身心因素,比如身体相关的减分项除了疲惫外还有身体不适和生物钟的影响,这两者在这几天都有体现。身体不适主要影响一到两天,而生物钟对我而言则是长期的。滑稽地是,这里的影响不是生物钟紊乱而是生物钟过于规律造成的——我并不希望每天早上八点准时醒来,且保持着一些疲惫感且无法再次睡去。我深知这种滑稽是宿舍糟糕的采光造成的,这种客观的结果短期内无法改变,只能当做加了一层debuff。这几天偶尔会波动到九点,但这种波动带来的又是紊乱造成的不确定性。理想的情况本是稳定地在九点醒来。或者我只能被动接受然后整体挪动自己的生物钟。但三月底之后的夏令时估计又会让我出现新的问题。
不过这篇文章主要希望讨论的还是心理的减分项,我把其称之为“焦虑”,这里是一种广义地用法,本身心理的减分项应该包括恐惧、痛苦、遗憾等负面情绪,但我把它们统一到焦虑名下,把焦虑当作原因,而把负面情绪当作焦虑的结果。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再次使用分类大法。
按照人与事的状态变化,我把焦虑分成了做事不同阶段带来的减分项。注意这里不是焦虑本身有阶段性,而是在完成一件事的不同阶段,焦虑在其中的体现。“完成一件事”这个大前提是蕴含在博士期间这个假设里的,因为在人生的其他阶段,或许并没有这样一种目的性。
所以焦虑被划分如下:
- 做了不应做的事的焦虑
- 将做而未做的焦虑
- 应做而未打算做的焦虑
- 没有应做的事的焦虑
这里的“应做”不仅指博士期间的科研、学习等事,而是指我认为值得做的事,即带来的(短期+长期)效益大于花费的时间成本的事。“将做”是指列上议程,希望在短期内完成的事。为方便讨论,这里把短期认定为一周以内(因为一周见一次导师,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分界线),长期则是以几周为单位。这四种情形对应四个阶段:当下、短期、短期与长期之间、长期。
第一种焦虑体现为负罪感,针对的是游戏、看剧等事后被认为是意义不足的事。这里要注明的是,并非所有的休闲活动都会被囊括,因为休闲时间已被认为是必需的且时长为一天半/每周时都是可接受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意义不足,如果玩某种游戏无法给我带来快乐,只是用来消磨时间,那么这才是意义不足的体现。如果时间和快乐能等价交换,那么在休闲的语境下这都是一种意义。
第二种焦虑如同鞭子,在五天半/每周的时间内打在我的心上,督促我不断向前,将时间投入到规划好的事情上。但为了和其他几类情况作区分,这里针对的是已列出的事情,因为科研可投入的时间是无穷的。所以更好的看待方法是把第二种和第三种结合起来。当科研有思路的时候受到第二种驱动,而没有思路的时候受到第三种所驱动着去发现新的思路,再转化为第二种。
第四种主要体现在休闲时间,这也是长久以来关于“生活”的话题想探讨的,如果不正视这种焦虑,那么要么走向第一种焦虑,把自己的时间变成垃圾时间,要么走向第二三种焦虑,且把自己变成一台无限运转的科研机器,等待某日的泡沫破裂。这里还涉及到一个短期与长期的矛盾:如果一件事被认为是短期内的现象,那么可以花费所有的精力在上面,而如果是长期现象,则必须考虑休息时所要做的事。
简单地列举与解释后要做的是将近期的事对号入座,找到近日心情低落的原因。上一次写文时遭遇的情况是,在短暂的几天内,始终有马上需要做的事,所受到的主要影响则是第二种焦虑和身体的疲惫。而这几天的情况则是第三种和第四种的混合。其一是因为进入一个新的project,还在摸索阶段,连要走的路都还没找到,能想到的可做的事都做了些许但不充分的尝试,剩下的主要目标其实是找出一条可走的路然后拿第二种焦虑带来的鞭子让我快速前进。其二是在休闲时间的应做之事中又做了几次尝试,包括现实向的纪录片、阅读《资本论》、看电视剧等,但效果有限无法达成长期的快乐源泉,且由于题材的严肃性给人的放松程度也有限。此外还要时刻应对第一种焦虑的冒头,目前我已经甚至第一种焦虑的必然发生,所以真的是一再缩减做无意义之事的倾向,随之而来的便是可供支配的休闲时间的增多,进而带来第四种焦虑。甚至我觉得,无法进行合理的休闲已经使得我无法投入科研再生产当中了,因为我觉得按部就班交差式的休闲并不能算作是休闲,于是一天半后还有一天半,休闲时间的界限也被模糊了。
有一种整体调节的方式是降低对“意义/时间”这个值的预期,但这如同饮鸩止渴,像是量化宽松带来的开闸放水后能有一段时间的充实感,此后则会无法复返地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形。所以我还是觉得要慎用。
在保持“意义/时间”的预期之下,可做的两种方式便是增大分子和减少分母。开发新的休闲模式等模式指向的事增大分子,已被多次讨论,而减少分母的方式此前则没有被考虑过。因为以往减少分母往往是被动的,比如出现许多不得不做的事(做TA、写作业、考试等),把95%的支配时间占比变成30%甚至更低,那么在自由支配的时间中显然有许多有意义的事可做。而我这里提到的减少分母则希望采取主动的模式。即主动地把95%的可支配时间下降到90%或者更低。这里需要被仔细地考虑,因为很容易掉入曾经已被多次尝试无效的陷阱。
其一是用运动等固定行为减少可支配时间,我一直对此十分抗拒,因为这些行为会对剩余的可支配时间带来整体的影响(身体疲惫,状态不佳等),且不太可控。其二是在心理上下降对可支配时间的预期,把减少的5%部分认为是不受自己控制的部分,不做任何考量而任其自然,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有点掩耳盗铃的意味,本质是把第一种焦虑以合理化来消解。其三是以漫无边际地思考或者联想填充,这种方式以前可能被无意识地使用过,似乎效果还可以,但也曾遇到一年前的“思考溢出”带来的痛苦,可以作为尝试的对象。这有一种调整心态至“悠然见南山”模式的意味,其实影响的是整体的心态模式。
此前思考过需要进行整体的认识升级,像高中时和大学初那样,让自己的思考模式甚至三观进行系统地变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实现这点的高效方式是阅读、思考、实践相结合。如今实践这条腿天生瘸了,所以似乎并不太可行。于是转向次一级的整体心态转变,这在去年的时候通过实践和思考(没有阅读)实现过一次,如今去复制肯定不现实,而尝试还是可以做的。这个思路其实是新开辟一条新的“意义”时间线,将5%或者更多的时间投入这条时间线,从而减轻主时间线的实现预期“意义/时间”的压力。不过具体的实行还处于混沌地思考当中,希望不要反过来变成第三种焦虑吧。
11:11 2020/3/8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