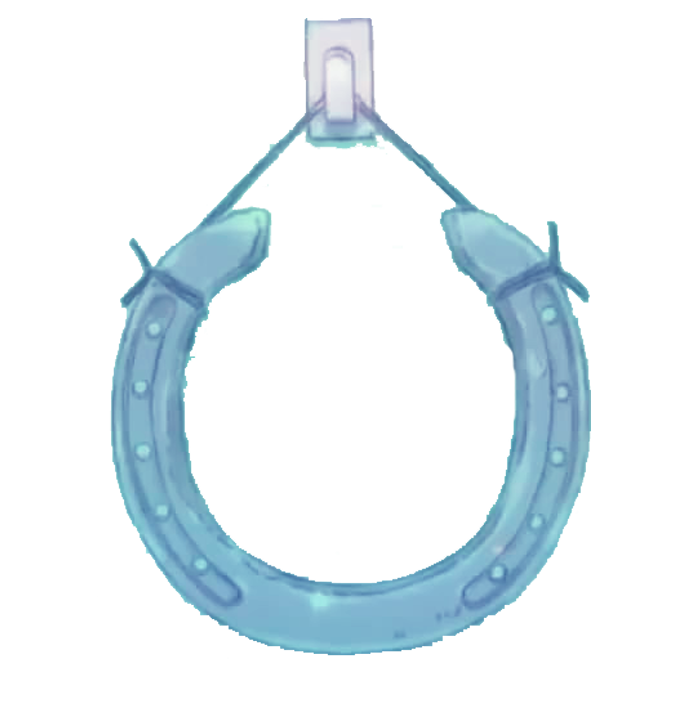行万里路,混乱的迷思
数月间,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东北、华北、中部、东南、西南、西北,一个个省份上的迷雾渐渐散开,一个国家的版图在我心中渐渐拼成。故土的概念,从海岸边的那座东方小城,延伸到了数百万平方公里。
生活的改变源自于生日后的第二天早晨,一个意外的奖项让我有了一笔可自由支配的“巨款”——虽然不足以让人生大起大落,但足以让细小的决定发生质变的一笔钱。当时我只觉得这不过是几个月的生活费。
第二个诱因或许是某条安利的弹幕,让我发现了《河西走廊》这部精妙而令人意外的纪录片,精妙在制作精良、叙事娴熟,让我知晓纪录片也可以令人着迷,意外在其中一集提到了南北朝时期,儒学在凉州(甘肃)的传播。一个我陌生的时代,一个我陌生的地方,发生了一件看似熟悉的事,传道受业解惑,却给了我一种强烈的错乱感。《河西走廊》一方面开启了我以纪录片了解中国历史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让我对地理对历史的影响产生了兴趣。
第三件事依旧是与纪录片有关,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中,提及当时的学生大多步行前进,数十日的户外经历,让他们对中国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一方面让我想到,广袤的土地上,城市不过是星星点点,而城市之间的世界,除了铁路与公路旁的树木,我从未关注。另一方面使我明白,许多理解与思考只有亲身接触实景实地,才会油然而生。大漠孤烟直的胜景,想象永远只是虚假的渲染,与事实有巨大的偏离。
于是在某次寻常的聚餐中,不知如何岔走的话题来到了假期的计划,在国内走走的想法冒了尖。大学以来的出行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信心面对独自的出行。近年来铁路的发展与公交/单车扫码的普及,让交通也不再是一个问题。于是,有钱、有时间、有能力、又有客观条件,一个失不再来的出游条件摆在了我的面前。
一开始只不过想略作尝试,选择了冷门地区个人行、旅途中段约好友的模式。而到熟练之时,已经能在个人行、见朋友、约出行三种模式间轻松切换了。不过就像前几篇文章谈的那样,其实以前的出行是带着要思考的问题的,了解各省历史,遍尝各地美食不过是一个副产品。但如今,当西部之外的省份(除了广西、台湾)都在我心中留下了一片记忆时,我终于可以用旅人的身份,走过河西走廊。最后这趟旅程的终点是火车可以到达的最西部的城市——喀什。
如今我终于回到家中,却发现一切都很平淡,仿佛出游的日子不过是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我的理性又告诉我,其实我完成(或者说推进)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了解我所在的国家。这种了解是多个层面的,这一次的主要目的是历史与地理,当然还有一些地缘政治。
我在走过几个博物馆后,忽然发觉,虽然互联网中有几乎所有的常识性问题的答案,但许多知识只有身临其境,或是在当地看到一个对应的展板,才会动手去搜索。举个最近的例子,当我坐在黄河边时,才会突然兴起了解黄河改道的历史,才发觉水的变迁也在历史有着不可小觑的一笔。
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重庆,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武汉,黄河与祁连山所夹的银川,这些都是地理位置决定城市构造的重要典型。国土辽阔,却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遍地开花地建城,只有见过实例,才让我对以往文明6中要在水边建城的原则有了更直观的理解。石家庄、徐州、郑州、长春、哈尔滨因铁路交通而兴,江西和湖南基本盘相似却因京广线的选择有了巨大差异;浙江福建看似都是沿海省份,杭嘉湖平原的存在让浙江有了更多的优势。每一处的现状似乎都可以说出个道理,但只有来到当地,才会发现这些现状,才会有探索的冲动,毕竟如果一切所见都符合原有认知,各种理论也不会向前发展了。
上述是地理影响近代的方面,而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影响,实际上往往被埋没在一个个历史故事中了。我行走的一个目的,便是了解所达之处的历史变迁,由此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历史。这种方式对春秋战国等乱世的理解尤为有益,因为乱世各国的发展会更受制于地缘。春秋晋楚争霸,秦齐做强,靠的是“金边银角草肚皮”,即这四国分别占据了东南西北,而在中原(河南)的一中小国只能任其宰割。其中晋楚尤为强大,前者归功于山西的“表里山河”,后者的得益于南方大片无人开发管理的契机。而战国后秦国翻身做主人,则又是四塞之地的关中帮了忙。历史变迁,“地利”实际上占了不小的比重。
这篇文章让我觉得难写的原因是,一路走来,许多感悟都是知识性的,我也不过是略懂皮毛,不敢卖弄,长篇去谈未免班门弄斧,而略去不谈又会发现,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所以便只把一些零散的想法阐述于此吧。连我自己都觉得写得乱七八糟的,有点配不上游遍大江南北后的总结性文章。但我心中确切地知道,这份经历充实了我的所见所思所想,而这种提升并非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能体现出来的,而是扩大了我思考的宽度,至于新出现的空间中会填入什么,则是未来会发生的。
走出熟悉的城市,发现不一样,也发现许多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部分洗清了原先许多的习以为常,同样生活在一片国土下的人,可以拥有千奇百怪的生活模式。而一样的东西我归于文化,这是千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一种共同的习惯。至于文化的具体内容我自己无法把握,借助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的一些观点,这是一种以情感的“心”弥合肉体的“身”以营造的一种二人(或多人)关系,亦即强调生活在群体中而非指向个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多地以吃来促进,于是书中得出了中国人(或者中国文化圈里的人)擅长在吃上做文章而英美系新教文化下的人则只认为吃是用于填饱肚子的结论。这个观点可做参考,毕竟以我所见的确如此,也许需要更多的经历去验证它。
我觉得自己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在走过中国各处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尤为加强,甚至许多时候思维中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前遗留的两个问题:如何关心他人,心寄托于何处,其实都依托于文化的背景。关心他人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是互动型而非单一输出型的,不同文化体系下的人,对关心的需求也是不同的,于是辨明对方所受文化影响,再用对应的方式,或许更为可取。或者说我对“关心”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体系下的,比如嘘寒问暖,偶有帮助,都是这种体系下的常见方式,而有效力度则与对方对文化的接受度与依存度相关。
而心寄托于何处则完全是中国文化下才会有的问题,因为在个人主义风格下,寄托给自己才是独立的表现,而在中国文化的群体性下,有一个外在的对象似乎才是更合理的表现。所以问题便转化为,(潜意识地)我是选择了更为传统的多人模式,还是更有英美画风的个人模式。这之中没有优劣,只是选择,这之中有个人最终偏好的选择,也有周围环境导致的选择。用这种新的方式,我姑且以取消问题的方式解决了此前遗留的两个问题。好处在于此后可以不必纠结于此,而还需要未来更多的生活去填充这种想法。
或许写得不好的原因,是情绪未到吧,以往畅然写作的背景都是郁结于一处而不得解,如今其实是豁然开朗的,便懒得向外展示自己的想法了,而且许多想法也不算很成熟吧。暂时就结于此吧,这一次不需要很强的“仪式感”,只是平稳过渡便好了。当然最终还是要庆贺一下,达成了“最北、最南、最西”的三大成就。
12:02 2019/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