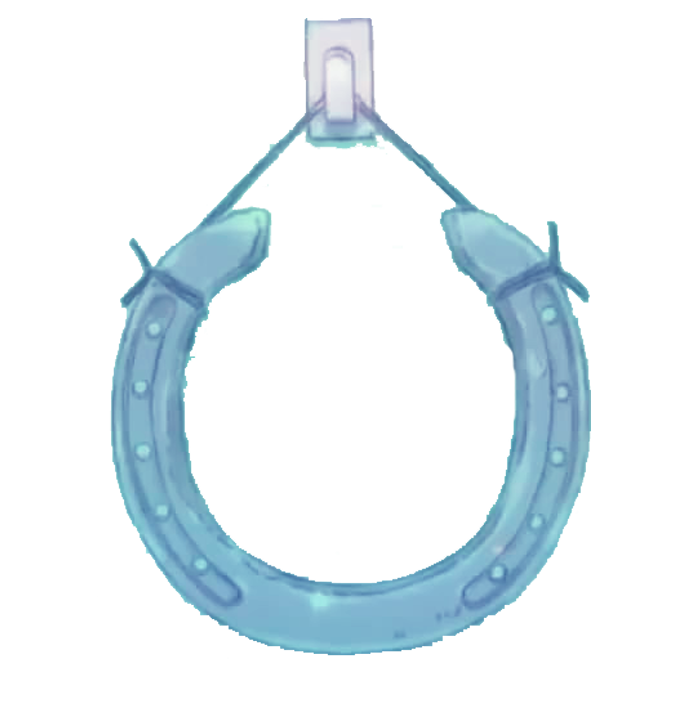务虚与建构
当我手里有一把锤子,我会不自觉地把遇到的问题都看成钉子。当我对数学的研究模式有些许理解的时候,我忽然想套在理解生活的方式之上。或许会有蹩脚的类比,但不妨是一种有趣的尝试。
近几个月来,我希望解决或者理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我心目中的“务虚”?早先的答案是“做之前并不去考虑最终能够得到什么,单纯凭借心中的愿景与冲动便做出行动”。但实现这句话的前提是,我需要明确“心中的愿景与冲动”究竟是什么。原先我恰好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便是“我希望自己判断事物的价值始终是‘对自己能力与品性的提升’,也就是注重内在的修养而非单纯为外在的表象”。似乎一切都立刻有了完美的解答。
那为何我心中还有疑问?症结点究竟在何处?其实这些才是真正的问题。我明确地知道我的思想状态不对劲,我感到自己像《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的主角一样,逐渐丧失某种人性的光辉。这不是输入几个核心观念的句子便能解决的,我逐渐丢失的,或许是一整套思维的系统。更确切地说,是这套思维的系统对我来说已经显得“过时”了。
原先我不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形,19年时,我曾困扰于朋友之间的关系。而最终我的解决办法则是,重构一套看待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模式,由此将以往遇到的前后矛盾之处以系统化的方式化解,给自己的行为逻辑给一个合理化的方案。相比原先我看待朋友的三条准则,我引入了更多的条件进行考量。这也是当时的我受到数学研究思维影响的结果:数学研究中,为了解决一个陈述简单的问题,往往会建立一个更大的框架,使得原先的问题在这个框架中变得自然,然后研究这个框架的途中,问题有时就被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种加大理论复杂度的模式看似会使得整个系统更为死板,但时常是数学家们选择的方式,因为大的框架意味着某种完备性,某些隐藏的桥梁便更容易浮现。
而现在也是,当我在现状之中乱撞而找不到出路时,不妨跳出来,试试重构新的思维框架。构建思维框架的过程,是对自己能力与品性的重要提升。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构建新框架和原先的情况还不相同:原先着眼于一个具体的议题“自我与他人”,而现在的“务虚”在构建框架这一行为本身便已经实现了。这正好应合了“做之前并不去考虑最终能够得到什么”,因为“务虚”本着眼于过程,而非结果。
但这么弯弯绕地说,其实还未切中主题。我不过是把对“务虚”的追寻化简到了重构思维框架这一行动当中而已。那要如何构建新的思维框架呢?近一年来我对数学研究的理解,则为这种构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办法。自小到大一大二,我在数学上所做不过是学习前人总结完善的理论,加之有标准答案的练习,到本科高年级,我需要学习近几十年人们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曾推导出漂亮的结果,否则也不会受数学家们一直关注。但与此同时,这些理论还都远没有到完善的地步,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往往也十分粗浅,只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探索。对于这些近人的理论,一个要点便是理解哪些地方是它们擅长处理的,哪些则是难以处理的,对于后者,是否有其他理论得以补充。而当真正进入数学科研中时,一种方式是平地造起万丈高楼,这当然困难。另一种方式则是在已有理论的边界做探索,寻求理论的进一步延伸。这种探索的前提是,摸清楚理论的边界是什么。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判断哪些事实不过是某篇文献上的结论,哪些事实是真的还让人没什么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许多理论的细节曾被包裹在黑箱里快速地略过,而当真正被理论的边线所绊住时,往往才会反过来一层层拆开黑箱,寻找究竟哪根线出了问题。与此同时,在理论的边界探索时,也需要时常关注同样所处边线的人们的成果。这类成果不如成体系的理论完整,也有许多冗杂的部分没有包装好,但却时常能给人带来最新的视角。这些新的视角有的又是另一些成型的理论延伸出来的,而从边线往回看,学习原先忽略的那个理论,往往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幸运的话,能快速地学习这个曾被忽略的理论并立马用到眼前关于边界的探索中来。
我希望将上述的科研经验套到思维体系的构建中来。我曾热爱阅读,高中时期有过“一本书为我打开一门学科”的感慨,大一大二时则是将高中时揣有兴趣的学科都做了了解,方式为上一门通识课、同时看线上相关的视频课与课程推荐的书目。大四时,还对原先不甚感兴趣的史地政做了“行万里路”式的了解,发觉同样的知识,在百科中随手搜到,和在博物馆的展板上看到甚至是博物馆长椅上拿着手机搜到,给我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原先单纯以阅读获取知识的方式在此得到了巨大的补充。上文中提及数学在本科及以前不过是在学习前人整理完善好的结果,到本科后期是近几十年的结果。而我对某门学科产生兴趣到简单了解,和我在数学中对某个理论方向产生兴趣到上一门专业课去了解,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原先在感兴趣的学科上所做的事,也可以被归结到学习和了解前人系统化、完美呈现的结果。我曾认为这个过程,相比我学数学的主业而言,是十分“务虚”的,因为它们的确能够提升我内在的许多能力,而且往往对数学研究不会有直接的裨益。
而后我曾纠结于阅读越来越少,甚至越往后,对其他学科的兴趣也逐渐减弱,因为我明白任一学科向深处挖掘,最终难免会像数学一样,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且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小,往往几年几十年才会突然有重大的理解突破。而庄子生有涯的告诫让我决定只选择一个方向一直前进。这个方向,便是数学,因为我喜爱它本身和它带来的职业生活,而又明白了我的确擅长它。在笃定这一方向后,对于其他的方向我便始终抱有浅尝辄止的想法。而且研究数学本身便是一件极其耗费时间与精神力的事,我便不再有勇气向原先学习哲学双学位那样,去做啃哲学家原著这种耗时耗力的事。至今我的“书后闲想”止步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半部的原因,也是如此。由于在数学上做出成果被我认为是一件“务实”的事,而当我将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投入到数学当中时,“务虚”消失的问题渐渐地浮现了。
今天原本想到一种解决“务虚”问题的途径,但局限于数学研究内部:既然了解一门学科的过程和学习新的一门数学专业课情况类似,前者曾被看为“务虚”,那么后者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务虚”。这种解释有个前提,便是抱着纯粹求知的心态,体会前人工作的完美展现,有时往往忽略细节,而着眼于较大的叙事带来的思维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几个例子便是代数几何里“相比于Objects,更重要的是Morphisms”,即事物之间的联系、所蕴含的结构往往比事物本身更有意思,辛几何里“局部辛结构平凡”,即所有局部结构看上去相同的东西,在整体上也会有所不同。我原先也曾受到过几门物理课的影响,其中“场比粒子更本质”、“More is different”的想法也让我印象深刻。我甚至写过 一些物理概念与生活的“蹩脚”类比。由于数学科研的不断细分,我对其他细分方向的数学理论并不十分了解,在见到一些有趣的结果或者概念时,听一门专业课作为消遣未尝不是一种“务虚”。
上面这一途径本已算作不错的解答,如果我的视角仅限于数学,而我立志做一名投身数学的学者的话。但在想出这一解答后,我又发现了项飚 的谈话节目。原先我曾对他有所耳闻,甚至看过他的一本书,而在现今的心境下听他与他人的谈话,又是另外一番感受。他谈及的话题,诸如“附近的消失”,是一个有趣的议题,其实也与我近日的生活相关,但我暂时不想展开。我更关注的是那种探讨的能力,我忽然觉得,我不愿意丧失探讨这种话题的能力,而使生活中处处充满着数学。我内心深知我不是一个全身心投身数学的人,而我博士以来往往“主动地被迫”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主动地被迫”指的是我刻意降低数学外的事物带给我的吸引力,使得数学成为我可以选择的事物中,给我带来的效益比、成就感最大的事,而数学的确这样回报了我,所以我逐渐形成了以做数学来活动脑内兴奋的回路,即使在没有外力要求之下,我脑内也会不自觉地去想一些未完成的问题、未来几天在数学上的打算。这或许是我对我理解的“务实”的又一层解读,而如今“务虚”问题显现,也便是这套行事方案渐渐失效的体现。近段时间来,我已不再可以降低数学外事物的吸引力,而却不知道能够代替数学的、拥有相近或者更大吸引力的东西是什么。我想与他人产生思维的碰撞、产生自己对世界独特的理解是其中一个选项。我曾经借修哲学双学位实践了这个选项,而现今则是又重新将它摆到了重要的位置。
回到上文数学各阶段与构建思维体系的类比,曾经在哲学上的阅读与思考像是对前人完善的理论的体悟与复现,而此后我可以更多的关注于近人与今人对世界与个人等议题的理解。由项飚的谈话有感,重要的是建构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去描述与指导我们的生活,因为现今的世界正在以超出以往的速度变化着。不像在数学上我已站在理论的边界,在构建话语体系方面我还是个初学者。一套优秀的话语体系能让原先隐藏的要素浮现,就像“附近”这一概念的提出与“附近的消失”这一现象的解读能够部分解释当代个人遭遇的困境,也有助于辨析什么是我们真正希望的个人化,它不是固守于乡土社会的小圈子,现代化与互联网让距离被更快的速度跨过,也不是成为被抛在沙滩上的一滴水,涨潮时万众欢腾,退潮时独自干涸。在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想我需要做的便是了解今人不甚完美的理论,探清其边界,再立足于边界,寻找一套自己的模式。
数学研究和构建思维体系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前者在直观的猜想后还需要用具体的技术与逻辑去验证,而后者的猜想往往随着时间便产生了自我证明的效应。一个话语体系构建的本身不仅让某个概念得到了明晰,有时也会反过来改变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但在最后一步之前,还是互有借鉴的,比如往后我的阅读不必纠结于以往的泛读,而是从某个边界的理论往回追溯,由此更快地理解早先的理论,反之现学现卖的应用到当下,如此或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也能够避免原先“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困境。
至此,我并未给出一个成型的结果,只是在原有理解的重述过程中寻找到了未来思维的方向。早先是“探索世界的丰富多彩”,此前是“认识自己的所感体会”,而如今则是“构建思维的系统体系”。
21:51 2021/1/29
系统更新至2.021c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