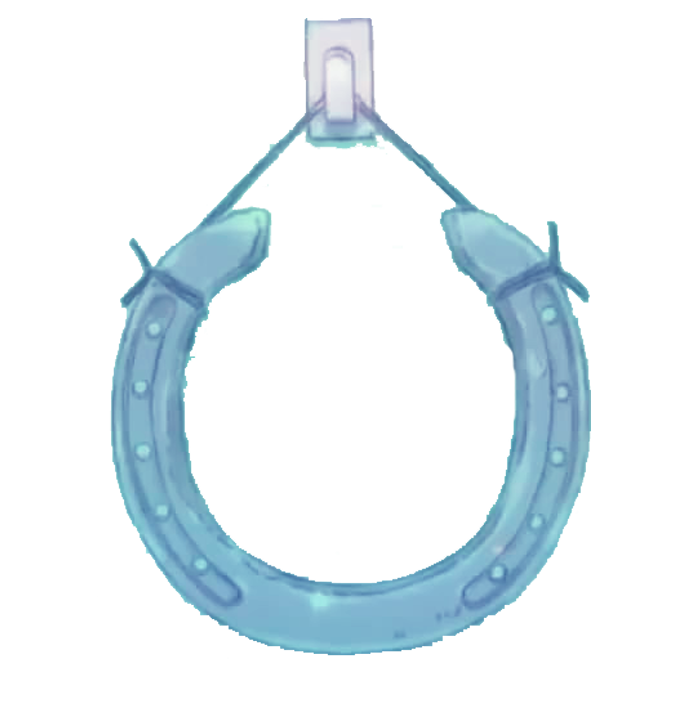身心的安全屋‖《不原谅也没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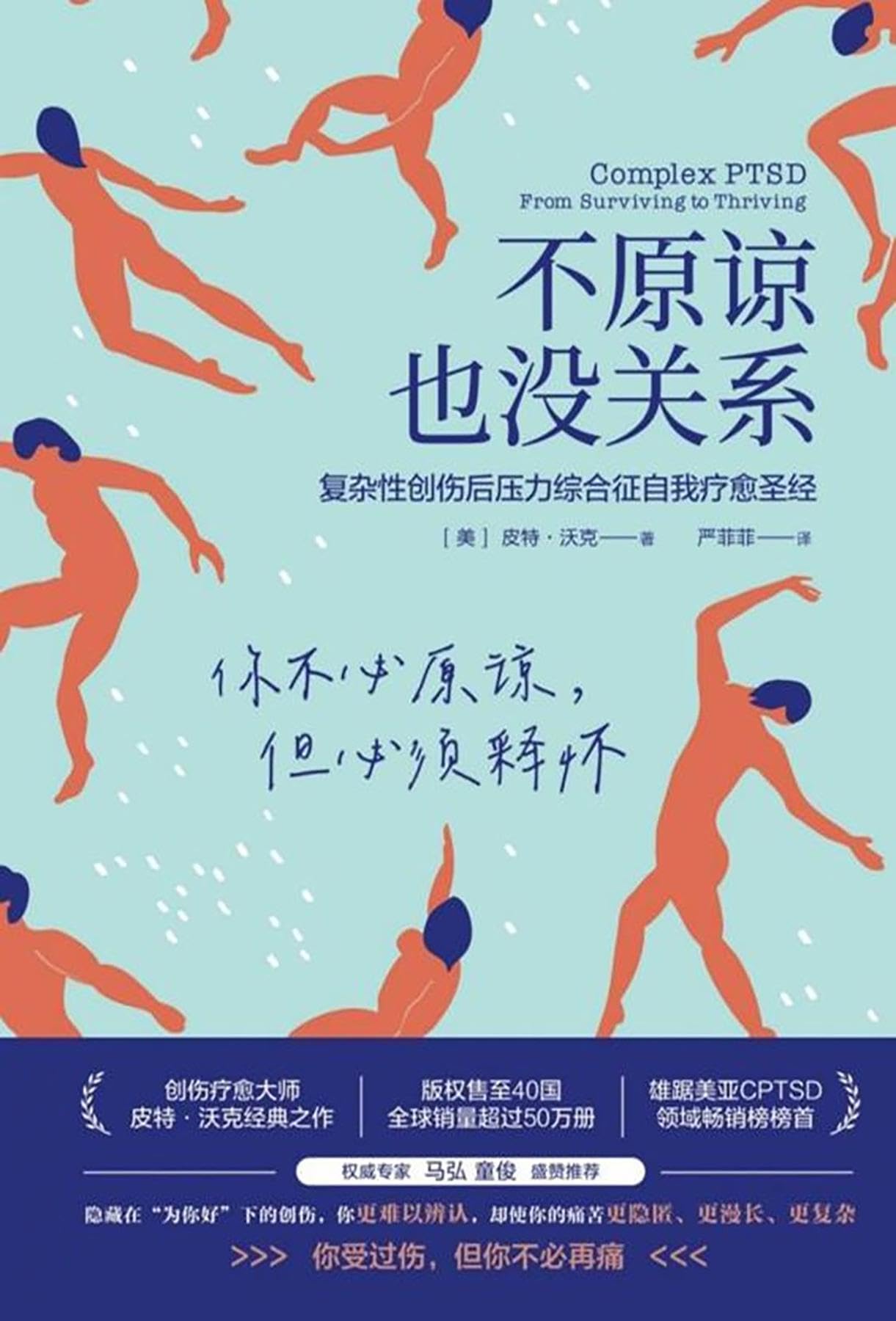
哲学能让人理解痛苦,而要在实操层面面对与处理痛苦或许还需要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辅助。在此时隔两年重启“书后闲想”系列而非继续写随笔,是因为我自认所面对的困境以无法用理性抽象的方式软化与应对,数次与朋友倾诉时受挫后也丧失了表达的欲望,最终选择了靠自己硬抗。借着书讨论至少有个依托和锚点,在兴趣层面做些抒发,也可以点到为止。
这本书源自于波士顿读书会活动时一位心理咨询师的荐书,探讨了与父母长期接触后形成的cptsd(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综合征)的症状与应对之法,是指向实际行动的工具书。过往我对心理学大礼包(星座塔罗算命等)不屑一顾,当重要的关系受挫时也会寻求mbti与各种心灵(毒)鸡汤作为承托。此前读到这本书时便觉得专业性较强,让我接受了以cptsd描述自己境遇的这种叙事,并尝试以此为发力点应对家庭关系,自认为有所进展便告一段落。近几个月主要面友情与爱情关系,将这一议题搁置,而当再度面对家庭关系时,仍深以为然,甚至有种系统化叙述覆盖零散的心理学礼包带来的整合爽感。吸收过优质的想法,再回望此前的心灵鸡汤,便觉得索然无味。于是,我坚定了将心理学等面向现实世界的学科作为护盾的想法,正如“社会学是一门防身术”,因为劣化的想法往往会在低潮期入侵人的思想,进而长远地改变人的行为与未来走向。
提到面向现实,让我想到遥远过去的某个大问题,即我自己最终的偏好是指向理论还是指向现实,当时的答案毫不犹豫地是理论,甚至对现实都没有实感。如今有些对现实的理解更改为“表相的看似不可更改的状态”,表相,指的是由思维结构与内心状态映照出的外部世界的样态,这点在低潮与开心时能刷到不同质量的视频之时被我认定,即世界繁杂,许多信息与渠道都能接触到,只是想法和心情决定了哪些东西能被注意到。看似不可更改呼应的是梦想的实现与放弃,实际上所谓的“现实”是可以更改的,只是此处的更改需要更高的能量,且这一能量实际上能够达到,只是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所以不愿用在这个上面罢了。类似于如果有一笔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一旦买了一个便会限制另一个。这种受限的自由,类似于定理的假设,反倒框定了其应用范围而使之明确。我做如此保守的假定,却在行为观察中注意到他人心中不可更改事物甚至不会被本人观察到,我也相信自己有些观察不到而习以为常的现实,此处也有个专有名词“意识形态”指代这些“默认”的实际情况。我要面对每个人的意识形态,甚至一个团体中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用另一种强硬的意识形态对抗,或者加入这种意识形态,是常见与轻松的做法,说得大一点便是所谓“沉沦”,而采取可被虚无化的意识形态,则会遭受各方面的攻击与影响,过往的攻击来自于普通的熟人,倒也能轻松防御,而现今的攻击来自于亲近的朋友不理解的质问,或者带有偏见与拒绝的调侃,当心情低落无暇对抗时,便也不得不选择采用疏远的方式。过往对许多议题都有着充足的理论自信,能够据理力争,可涉及讨论感情时,便不得不展开脆弱的一面,否则不过是场面话与社交礼仪罢了。
稍微有些扯远了,回到这本书本身。相较于第一次读,这一次面对书中提及的症状,如情绪闪回、毒性羞耻感、战、逃、僵、讨好,自认为已改善不少,尤其是情绪闪回,如今基本能够在显意识中隔绝,即能够以轻松地态度谈及过往的许多创伤事件。展现脆弱与自我哀悼的能力也已经纳入了工具箱的一部分,我能轻易地在动情的影视作品与实际场景中流泪而不以为耻,也逐渐学会关起门来自己一个人疗伤。此前随笔中讨论较多“被遗弃感”,在书中也被着重讨论,让我怀疑这个词是否是在看完书后才联想到与具象化的。在与朋友的讨论中,我意识到谈及有些话题还是会让我不自觉地进入创伤的情绪,但如今已能够察觉到并根据场合转移话题还是进一步释放,这使得过往不可名状的一团巨大的悲伤,被打散成为一些细小的部分,虽然短时间内还无法完全消化,但过往走出某几段感情,最后完全成为轻松笑谈的经历,让我相信这不过是时间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历练罢了。如果过往的悲伤彻底被抚平,倒也少了些脆弱的部分与新的朋友产生联结。
被遗弃感的缓慢消解,来自于安全屋的构建。这个词来自于某个朋友,我曾尝试构建共同体的安全屋,如今却也接受安全屋首先需要是一个人的安全屋。说重一些是“他人即地狱”,说轻一点是产生联结便会产生不确定性,而安全即消解与应对不确定性,我相信某一联结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做到这一点,但如今我已被心灵鸡汤洗脑地决定自己先建设独属自己的安全屋,再试图开辟新房间为他人遮风避雨,而必要的时候保留把所有其他人请出去的选项。从罗小黑电影中挪用一句话“和平需要强者的主动”,我向往和平,我也学会了主动,我也还需要尽力成为强者,包括心境层面。一味不择手段追求力量的角色时常被当作反派,于我而言则是放弃一些品质会让内心有更大的动荡,且技能树纯点力量的话在效能比上不高。
此处的安全屋首先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一个可以独自待着的住所,加之舒适的气候与便捷的饮食。近期为新住处添置大小物件,再把“外人”包括父母都请出去的时刻,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在这一环境中,我无需面对他人,只需面对自己,身边所及的细节也都指向着平淡美好的回忆,而非过往痛苦与创伤的时刻。如果有人想在这一空间内创造负面的经历,我也会努力第一时间将其请出去。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空间内是“主人”,而所有其他人都只是“客人”,实际上还是要看我眼色行事。我可以适当让渡各空间与物件的使用权,甚至为客人准备舒适的床铺、书桌、沙发与充电线,但我保留收回的权力。此外,某位朋友的调侃“有些人会在车里消化完情绪再回家”也被我实操了一下,不得不说停在车位里的车本身也有创造额外安全空间的效果,且空调、灯光与音乐直接指向的都是情绪层面的。如此又额外收获了一个物理层面上的安全屋。我也逐渐明白房与车对许多人的吸引力,不过对我而言在赋魅前直接祛魅而快进到实际层面的享受了。
而心理层面的安全屋则需要更为精细的建设。一个点是我终于意识到长期以来只在浙江才出现的鼻炎原来不完全是气候原因而是家庭环境的压力所致。我也能通过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反过来判断环境与身边人是否相宜,这一列表中已有头疼、胃疼、肚子疼、鼻炎、疲惫、抠手指等活动,我可以通过过往经验来判别对应负面状态的种类与来源。对于悲伤/痛苦,我已能够及时观察到并有少许成熟的方式应对,在无法应对时身体也会以解离与麻木的方式保护自己,而愤怒/不耐烦、孤单/依恋、压力/紧张则是三种我无法及时察觉与应对的情绪/表征。物理安全屋的特点是有个空间允许自己延后应对,也如泉水般能让自己缓慢回血,所以心中会认为当时不处理情绪也不会导致灾难,只是要消耗更多精力与时间罢了。而心理安全屋的建设则是对这些情绪建立成熟的察觉与应对机制,并不压抑它们,而是用可控的方式排解。
此外,书中提及了“内在批判者”和“外在批判者”两个概念,指的是创伤应激后,在受鄙视的自我与浮夸的自我两极摇摆,因而要么指责自己,要么指责他人。遗憾地说,过往几个月我确实陷入了这一境地,并以断言式的方式在其他朋友面前指责我伤害过我的过去的朋友,如此似乎能发泄让自己好受,但实际上我还需要承担自己看走眼的自我批判,看似对他人的发泄实际上是再度对自己展开两重伤害,利用受害者的方式让自己感到道德层面的安全与渴求接受怜悯。然而过往与现在的我都深切地明白,这只是徒劳,只是我处于极度低潮期的表征,甚至对他人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对于伤害过我的朋友,我目前采取的自认合理的方式是从某一节点后疏远,并将这一节点前对方给我带来美好回忆的能力、愿望、梦想都加以实现与祛魅,由此这个人在我心中便可插上墓碑,我也可以将其当作一个新的人来接触了。因为其美好品质已能够被我祛魅,原先吸引我的点也大概率会消失,所以对方需要发展出额外的吸引点才能够展开新的一段关系,否则也只是普通熟人罢了。如此无需在物理层面将其抹杀,而在心理层面做到这点,似乎是原谅了物理层间的当事人,实际上在心理层面断绝了原谅的机会。借书名做个结尾,便是“不原谅也没关系”。
12:24 2025年7月30日
试图不定期更新书后闲想的
叶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