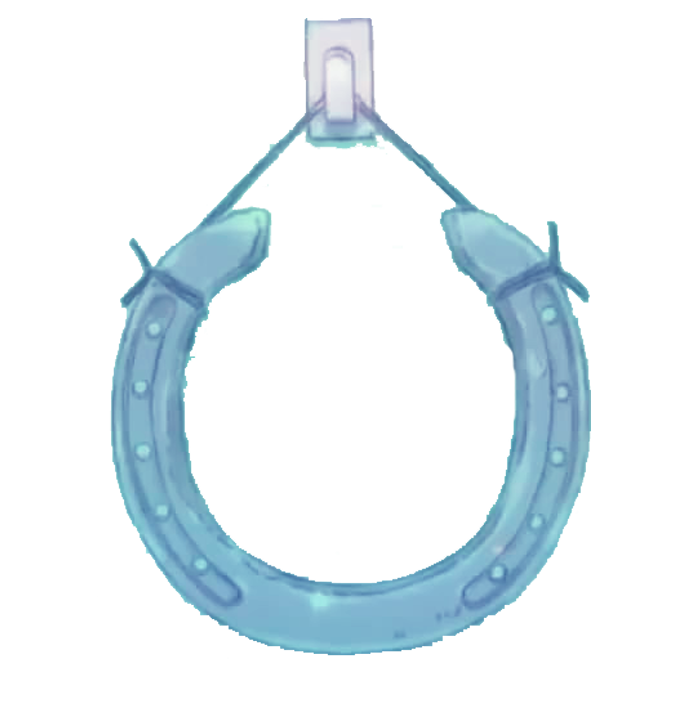自我与他人-续
这一篇是接着上次的大话题而谈的,但时过境迁,看事物的角度也早已大不相同。六月底的时候曾对“与朋友相处”这一点更为系统化的理解,但由于忙碌没有写下,好在留下了一些简要的提纲。目前复述必然不及此前,但也稍作叙述吧。
自我与朋友
上一篇仅仅开了个头,得出的结论简单概括一下便是,社交总容量有限和需求下限不为零。此外便是关于朋友的部分,这部分比较混乱,也是由于当时没有特别想清楚吧。
在去往中国最北处之前,我又遇到了一次友情的危机,不过这次似乎不能算危机,而是更像改变我观念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一次旅行让我想明白了生活对于我的意义(阶段性的),第二次旅行让我想明白朋友对于我的意义(也是阶段性的),这让每段旅程除了路途上的含义外,又多了一层精神与思想上的回忆。这也使得我在第三次旅程出发前也给自己设立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要到这部分写完,才能够更加清楚地叙述。
回到正题,鉴于此前的系统化研究自己感受的方式,我在列车上首先回顾了我的所有样本——从小到大所有能够与我称得上是“朋友”而非同学/同事的人,以及我与他们之间的经历,我在这些经历中对他们自然而然地态度。首先样本容量并不算很大,因为最终我发现满打满算可能也才六十多人吧,不过这里刨去了大量被埋没在时间洪流中的,阶段性的朋友,亦即,如果目前列出一个大致的核心朋友圈子,可能大致也是这样一个数目,虽然部分朋友在短时间内没有什么大事不会去联系,但一见面还是能瞬间拉近距离的。
其次我回顾了一下此前的模型,即三要素模型:轻松交流、深入讨论、兴趣相投。近半年来所遭遇的事让我如鲠在喉的点,即是我与朋友的经历以及我对他们的态度与我此前的模型产生了矛盾。有些人能做到这三点,我却在心中并未将其当初最佳的挚友,而有些人在一些事上做得不够,却让我更值得信任。于是以上这一经验性的模型需要被改变,当然我的笨办法便是,引入更多的变量。
新的模型有三个维度:交心程度、认可程度、关心程度。
三要素模型对应交心程度,拆解一下为五项:排解、交流、出行、日常和帮助。对这五项的理解,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渐进式的,即同学/同事间的帮助是最初的一个契机,而日常见面与一同约出行(旅行或是简单地约自习、看电影)是成为朋友的一个过程,但在日常和出行中也需要深入交流,并且在出现重大的事项是能够参与排解,当然这又是情感意义上的帮助。第二个层面是互为辅助型的,能够自然地深入交流以及相互排解是成为朋友的一个标志,但日常交流、相近的兴趣也是在平时互相拉进的方式,即这五项满足的越多,则交心程度可以判定为越深。这部分主要是对此前模型的一个重新表述,而另外两个维度的引进则是更为重要的(自我)发现。
认可程度主要是指自我对朋友的品格与特质的认同程度,按递进关系可以排为把握原则、办事靠谱、有所见解、自成体系。此前发生的一些友情崩盘事件,原因在于认可程度的崩塌。即我认为对方的某些处事原则与我发生了分歧,比如安全性问题,比如对待朋友应有的态度问题。当然这个维度的引进部分意义也是为了解释交心程度较高但仍会出现友谊裂痕的例子。我曾经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看重朋友的人,对于有些朋友,如果发生重要的事,我甚至可以排除掉其他的事,将其放在当下的第一位。而如今我却觉得,原则性问题是最后的底线,当然我个人的原则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但如果触及我个人的底线,那我觉得造成的伤害会是无法弥补的。
办事靠谱往往是在日常帮助层面一点点积累的印象,以至于在遇到某些重大事情时认为对方可以托付。有所见解则是对方至少会对生活中的事有所思考,而非懵懂地随波逐流,当然自成体系是一种更加完善地存在,从这样的人中我能学到很多自己所不具有地特质。大部分人不太被我当作朋友是由于根本无法与之谈务虚之事,而一些人被我当作挚友即是其在某个关键节点说出了重要的话或是重要的行为。
第三个维度是关心程度,这一点是此前“关心”问题的统合或者重新表述。按递进关系可分为各自为政、出事时会补救、愿意倾听、主动关心与在意我的想法。这一维度的引入部分也是为了解释之前模型的反例的。当然我的朋友中也有许多正例可寻,我与某个朋友的关系的转折源于某次用心的生日礼物,而与另一个朋友的关系的转折源于某次紧要关头地关照。生活中大家往往各自忙碌,愿意在你情绪低落时听你倾诉的人本就不多,而主动帮人解开心结的人真的是屈指可数了。原先我曾对主动关心有一些抵触或者叫不适应,但我现在觉得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真的很强,毕竟要冒着这脸贴冷屁股的风险,所以我还是希望尽可能地回应那些,愿意花时间与我交谈、邀请我出行、在意我的想法的人。当然另一个极端,各自为政,则是我与许多朋友的关系跌入零点的原因。我认为我的想法对其已无足轻重,说得不好听一些,会有一些工具人的感觉。
在这三个维度之后,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是否会有其他新的维度,使得我的模型并不完备。当然考察此前的数据后,自认为大致还是吻合的,恐怕模型的不完备之处还得等到新的友谊危机的出现。
我也曾想到信任程度这一维度,但我发现这一维度其实是被以上三个维度生成的(数学脑的说法就是线性相关),比如能够与我交流、办事靠谱、愿意倾听我的想法,那么我的信任程度自然会得到提升。反之当以上三个维度出现问题时,信任也就无从谈起了。但信任程度能否和友情之深的程度划上等号,或者说友情之深的程度与以上三个维度的相对关系是如何的,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量化问题。此外,以上三个维度是否相互独立,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但不论如何,这个模型暂时是被我接受并运用的,即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包,遇到新的朋友时可以调用。当然建立模型的一个新的作用是,把自己作为模型的受体去考虑,即,假设我遇到另一个用这个模型对待我的人,我要如何去做才能与之成为朋友?这种模式不完全可行,因为不同人的模型毕竟不同,但至少可以借此来与那些和我更相近的人成为朋友吧,以减少友情的冲突。除非前提是,两个持有相同这样的模型的人会相互排斥。
于是新的问题便诞生了:如何对待他人,一方面是现有的朋友们,另一方面是那些可能成为朋友的人。交心程度经过多年的关注与练习,于我而言相对来说更为熟练,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敢和他人说话、不敢结交新朋友的初一少年了。出国交流时的经历也让我在打开深入交流的话题上更为积极主动,这也至少保证了现有朋友之间,不会因为不敢谈而造就隔阂。
对于认可程度,要做好的便是不断地完善自己,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够我近日发现的是(其实上次香港之行便发现了),使他人认可,除了建立完善的个人体系,做事靠谱,不做“鸽派”外,还得提升自己的表述能力,即表达、展现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合理展现自己特殊一面的能力,闭门造车还是不行的呀。
而关心程度,则是我认为自己最为欠缺的,按以前的话题说便是,我不够热情,在与陌生人交流间更注重自己一些。而我也不太知晓如何才能称之为合适的关心他人的方式。关于前者,其实大致有很好的样例可以追随,但只是还没有迈开那一步,或者更深层次的,需要在心里上迈开那一步。对于后者,我曾在第三次旅行之时与朋友探讨,以此学会了一种新的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虽然不一定行之可效,但能给出一个解)——找极端。当时找到的两个极端是一个是对父母的关心,一个是那种借关心之名要挟的病态关系。我当时对两者都能给出直接的体会与应对措施(当然如今看来可能也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也是当下的一个主要问题吧,在此不详细展开),但这种方式的弊端是,两个极端间如果只是以线性模式理解,难免会有些偏差,或许不如我的取多个点,然后尝试用模型拟合来得好。
不过其实这个问题在于,我根本还没有办法问出一个“好”的问题,即有时我得到的答案并非是我想要的。这也涉及上文所言的表达能力,所以虽然第三次旅程已经结束,但我甚至连“大问题”的表述都还没搞清楚。好在第三次旅程的大部分行程都与(不同的)朋友一起度过,所以算是第二次旅程所想的一个良好实践,结果当然很棒,旅途也非常开心(甚至高于前两次,虽然所经之处相对不像往南往北更有深刻含义)。换个角度来说,对我而言没有写下来时,模型依旧是懵懂而未打包的(就像有idea也得写成paper),所以直到今日,在朋友这个问题才可以被认为有一个阶段性的进步吧。
但这第二个大问题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光是探究清楚朋友必然是不够的,近期的许多混乱的想法已经有些不愉快的小心思也是在他人这个集合去掉朋友这部分之上的吧。
寄托自我
第一个大问题“生活的意义”中,我不过搭建了一个大的理解框架,许多细化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讨论以及纳入体系。有些也会与第二个大问题有些交集,毕竟所有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变更都是建立在生活在时间中的流动的。
上文提及的他人去掉朋友的集合,尝试着划出几个大的部分便是:亲人、喜欢的人、同事(同学)、一面之缘的陌生人。这篇文章并不会对这些部分做系统性的展开(还得留给以后),但会有所涉及。
如上文所言,走向北方时的那件事,是改变我观念的最后一根稻草。将自我与朋友的命题明晰后,这个问题也越发突出:我发现自己的心无处寄托。
当理性与逻辑越发侵入情感,原先模糊的部分被明确,但其实也在被限定。仿佛交朋友就要遵从如上的原则,一条条的检验与实行。而我也知道这只是一个指导方向,在未来遇见相似情形时不至于在经历相似的心痛。这其实不过是给自己一个解释空间,告诉自己这些人因为触犯了这几条,虽然在其他维度做得很好,但却在我心中划下了伤痕,朋友的关系也被划定了一个上限。如果说在这个层面,其实是改头换面的放不下。而我遇到的问题或许更为不同,或者说在个人体系上更为重要:将心寄托在他人身上,值得吗?
这么说十分模糊,什么是“寄托”呢,以我当下的理解,是生活处事的一个最终导向,举个具体的例子,以往我与人出行,在意的是和谁、旅途中谈了什么、共同创造了什么回忆,反推回去要和谁约出去玩才能让这次旅途快乐而有意义。这件事上,最终寄托便是那个要一同出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旅途糟糕,只要出行的人们觉得创造了独特回忆便不失精彩。而如今心无处寄托,只得交还给自己的体现则是,出行是为了给自己创造更有意义的回忆,以行万里路短暂地代替读万卷书,让自己对这个世界又进一步的认知。在这种心态下,和谁玩不过是自己旅途方便,与他人一同出行也不过是丰富自己的经历,最终的目的都指向自己,而无关他人的感受。
上一部分所言,学会关心他人,其实也是希望在这一方面打破,但可能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于朋友,我或许大致能够摸索出些许关心的经验,而我失去了那些值得“特别关心”的人(这句话不是绝对而言,而是相对而言的,因为这次出行在朋友见面、一起玩、告别上都非常的完善,所以其实和此前那个大问题时情况相近,这是“幸福的烦恼”)。
如果寄托指向他人,那么便会有一种愿意与那个人分享所有的经历、情感、想法的冲动,而指向自己时,这些东西便不再会有多谈的愿望,需要谈及时大多是为了烘托某种状态或者得到某个自己想知道的答案。反过来而言,我的生活越发变得独有。原先将我的朋友对我的理解和与我共同的经历拼凑起来,或许能够得到一个大致的我的图景。而如今大片的个人出行经历与独自面对的事物,让我的感受越发难以与他人(其实是我当下的朋友们)分享,因为需要更多的前置条件的解说,有点像数学学到后期,甚至没法让同为数学专业的同学听懂。这一点又涉及表达能力,因为如果表达能力有所提升,便可以高效地让对方理解自己当下的处境。不过我现在讨论的问题的不在于表达方式的缺失而在于表达欲望的缺失,我不再会热情地向朋友兜售我的新看法,旅途中遇到的新经历,仿佛我预先假定了只能唱无聊的独角戏一般。于是,我觉得能够理解我的难度,虽然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提升,不知道下一次是谁在桌子那头,听着我手舞足蹈全心全意地讲述自己才懂的快乐。
敢爱敢恨
其实直白来讲,上述的状态不过是不敢爱了。寄托蕴含着信任与依靠,每次受挫都会提升这两者的界限。我曾经提起过一个话题,即让自己变得更加直率。我想在我的话语体系里,直率即是敢爱敢恨吧。敢恨这一点好像已经被生活调教的很好了,原先我曾是一个相信所有关系都会有转机、一切不愉快都是暂时、以诚能够换到诚的人,觉得那些看上去值得讨厌的人或事都可以将心比心去理解,而如今寄托指向自己带来的一个弊端则是,不愿在换位思考上多下功夫了,不喜欢的事,就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悦吧,何必憋着让自己难受呢,排面上的维护有事也会懒得。开门见山有事似乎是最快捷的方式。
但敢爱这点,似乎并没有什么进步,反而有了更多的阻力。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生活趋向点——事业。对原先的我来说,情感是高于事业的,因为我对我的事业(数学)没有那么深的依赖,将它划入理想生活的一部分也只是因为它能给我带来的东西恰好与我想要的相近(探索世界、为自己工作、时间灵活、可以四处游玩开会)。而由于博士申请的变故,我的事业不再只与过去相关联,还和未来扯上了关系,即我透支了部分未来来满足现在。这样的结果即是,我至少在未来某一阶段(三五年),与我的事业绑定了,它不再是随时可离开的,而是值得我重视的。这似乎是我变得现实的一个重要节点。
于是便更不敢爱了,原先的问题只是愿不愿意去爱,而如今还加上了能不能够去爱。因为在我的认知里,爱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亦即需要为此付出与承担责任。而当我的肩上有了一份事业的担子时,我还可以挑起另一个担子吗?一个朋友问我说:你要做牛顿吗?这当然不是指我要成为天选奇才,而是问我是否为了学术而放弃情感。他的第二句话是,要当牛顿可要先想好了。这话的背后,承载着一个事业与感情的选择。对大多数人而言,事业与感情是并进的,而对我而言,在事业上有太多沉没成本(我知晓是本应不去考虑的沉没陈本),而感情却从未给我正反馈,在将心寄托给自己的大背景下,似乎专心事业(至少短期内)是必然走向,而我即在岔路口徘徊吧。
互联网的引入,让人与人的接触分为文字、语音、视频、面对面四种。所给人的亲近感依次递进,曾经某个主动打来的电话、某个主动划开的视频让我惊讶之余而又欣然接受,而如今连与父母的交流都从面对面、视频退到语音甚至有时的文字。人心之间的距离就此变远了。
21:58 2019/8/13
不知所爱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