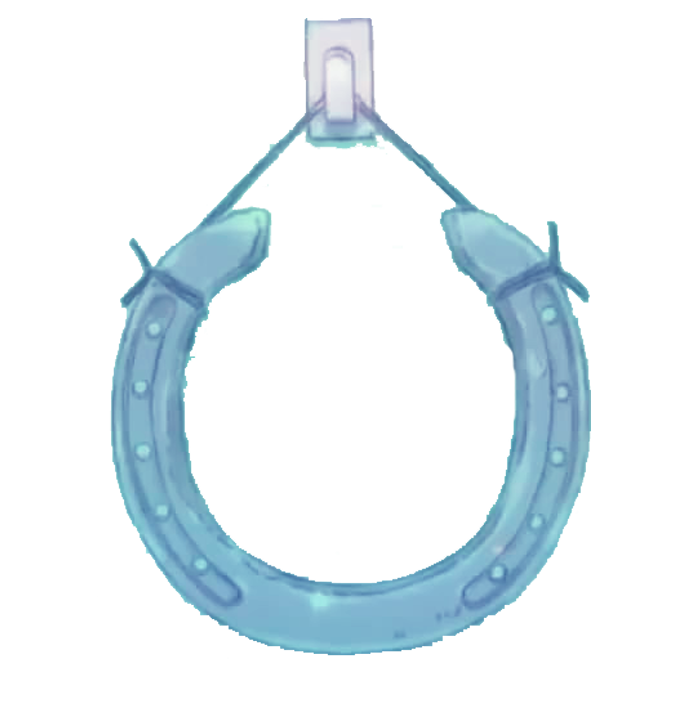情与利
自再谈他人 之后,我与他人的关系的新模型在不断地更新和深化,最初只是在同事与朋友 这类具体形象上展开区分,自恨与原谅 中理性这一强大的力量回归之后,如今已经可以在抽象层面谈论对他人的区分,结果的适用性范围也从针对具体某几个人上升到地图炮了。
其核心变化点便是这里 提到的对人性无条件信任的丧失,由此将某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归结于“人性的弱点”这个大垃圾桶而不再深入讨论,而最多采取观察、了解、甚至观望的状态。如此假定是我认为我已很难用三阶导数为正的方式对抗幂指数增长的来自社会层面的困难,所以退而求其次先给自己画个圈,在自己可掌控的范围内以正的二阶导数再提升些许能力,试图增长到能够清除过往历史问题的状态,以此至少不为人生的前三十年留下遗憾。
于是在理性、感情之外,第三个重要的要素,即利益被加入了思维框架。此时和第三容器中“指向自己”并不相同,因为那时感性遭受压抑,使得理性指导绝对利益最大化,但与此同时我在回答理论与现实时,仍旧倾向于探讨理论。如今则是理论指导现实,使得现实作为理论的目的所在了。与此同时,感性也不再被压抑而是能够在合适的场合收放。我不再期待营造“上头”时刻,但仍对上头时的体验抱有兴趣,只是平时的行为往往被当做储备利益的余兴节目。
此处的利益并非单指现金或者资产,我对这些东西并无手段之外的兴趣,即秉持“钱能解决的事都是小事”的观念。在本科期间,利益或许主要是信息,博士或博后期间,利益应该主要是机会或人脉,而如今我已对八卦或者信息贩子毫无兴趣,因为Ta即不能让我通过对话了解Ta本人,也不能为我提供足够有价值的信息,即我不相信社交市场上的信息有效性和浓度。同时,我也对逢迎式的所谓向上社交表示不屑,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攒了足够多的筹码,便不想靠对方的施舍,而是通过利益交换来达成共识。事实上,对这两者的斩断是我与父亲,以及一切广义社会性男人(有些女性也可以成为社会性男人)的决裂。过往听从或者受影响,产生的这两种行为让我感到恶心,甚至对同一个人,采取社会性男人的方式和采取我自己开发的互相了解的方式,能够达成不同的效果,让我觉得与人交往的打开方式十分重要,充满“爹味”或“油腻”的人往往并没有如其所想收获到更多所谓的利益,只是在自我满足与沾沾自喜层面上收获颇丰。
我上述所指我关注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般人口中的“交情”,甚至取个极限,便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然而我扔把它们称之为利益,因为我看重的情是浓重的,不仅是欣赏,更是相互吸引、相互支撑,甚至是定义和影响我的特质的来源。能如此划分的基础是,我自认为已经体验过许多交情之上的“人间自有真情在”,甚至能够为真情划分序列,即情这个世界并不萎缩反而十分广大。据我观察,对大部分人而言,交情与常规利益的世界已占据生活的大半,而真情中只有少数数据点,才会有白月光的说法,也无法深度学习出一套关于真情的理论与行为方式。而我至少在过往的不懈追求与挣扎中,以各种角度与层面心碎与心痛的方式积攒了许多负面数据点,也在近一年来积累了一些正面数据点,多少已经能够谈论我心中拟合的真情理论了。其直接的表现便是,我可以轻松回答“爱是什么”这种问题,当然另一个“人生的意义”这一问题也被自然推出。只是进来在某一饭局上被连问这两个灵魂拷问,还是让我对波士顿的心态多少产生了些许升华,因为北京的基础款社交氛围已然不足波士顿的真情浓度。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波士顿,并没有太多的留恋,甚至连感伤、遗憾、如释重负都没有,只有麻木地在飞机上睡觉,随便铲几下便把波士顿的生活埋葬了,只有表露真情的朋友才会在可见的未来被移栽到新生活中。我当然也时常被问到“为什么要离开波士顿”,我每次的回答都不尽相同,或者我挑选着提问者能理解的方式来回答,虽然每次的答案都是在某个层面上真实的回答。对于我自己,实际上我没多大兴趣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或许以画个句号的方式,来个定性吧。
在波士顿的我,所能积攒的只有利益,可能相比于国内常规社交场所,社会利益(信息、机会、人脉)与交情意义上的利益的积攒更为高效,换句话说便是“常人”口中的“更纯粹”。而事实上在我的职业上财产利益(现金、资产)五五开,对其他工业界的职业而言应该优于国内。而利益对当下已度过第三容器的我而言只是余兴节目,我实际上追求的是真情。或者更玄乎一些是真情的可能性,即新的表现形式。这已经超脱浪漫的范围,因为浪漫大部分情况下是来自于影视文学作品的具象化,或者说“常人”的想象受到作品的局限。而根据六月份我对某人回答时意识到我所体验的真情已经时常超越带有浪漫化滤镜的影视作品给我带来的感受,我便不再追求复刻或者模仿影视作品,而只将其作为理论性的参考,甚至只是了解“常人”想象的方式。
我多次提了“常人”,一来指向《存在与时间》中的沉沦,所谓对人性信任的丧失便是我已接受身边大部分人自然而然的沉沦,也明确自己目前不会随其影响而沉沦,所以暂时不必为“沉沦的必然性”而担忧。二来指向尼采所谓超人,我倒不想做超人,因为我仍希望在常人世界中筛选出还未沉沦或较难沉沦的人们接触,而非脱离社会去发明新的人类范式。后者更像是某种人类学的视角,以融入的方式观察与了解社群,但同时实践自己的研究,只是这里的田野调查并非跑到某个深山村落,而就是身边的“常人”。历史上居高临下的人类学广受批驳,所以我也不希望采取一种超人俯视的姿态,而是考取人类资格证的求知心态,只是这些“人类学”知识不指向兴趣本身,而是理论的数据点罢了。我对酒及相关的文化与行为的兴趣变来自于此,公共空间或者社交聚落的构建则是一个更宽泛的议题,当然还有诗人、导演等文艺作品生产源头的调性调查。这是上一篇文章中梦想接连不断诞生的原因,因为它们都是“以人类学视角研究社会”这一大方向的一些具体分支。
在这一层面上,波士顿的“可能性”就少得可怜了,一来因为我由于语言、文化、个人舒适度层面,选择将自己的社交圈限制在华人群体,此前额外加了个留学生、甚至数学这一限制,使得圈出的人让我不感兴趣,放宽两个限制后,真情多少能够冒头,但华人在波士顿的比例让我无法从社会层面,最多是社群层面考察研究。相比而言,北京是个更广大的试验场,我试图带着波士顿打磨的与人独立接触而又以真诚建立沟通桥梁的方式在北京筛选出更多真情的数据点,以此深化与延拓我关于情的理论探究,当然最理想的情况肯定是能让我再度“上头”,像数学一般再度找到人生的第二方向。
与此同时,数学作为职业的优点,以及近来国内数学界的新观念的形成,让我无需在社会利益角度花工夫,而大多情况下以交情的方式换取我在数学上的进展,这仍旧是常人视角下可接受的行为,或者正是数学人的理想状态。鉴于目前我身处奖励关的伪gap时期,我着实应该使用这段时间,进一步打开真情的世界。我的精神状态也允许我能够再度心痛甚至心碎,那便勇敢地体验吧。
11:54 2024年11月27日
切真活着的感觉真好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