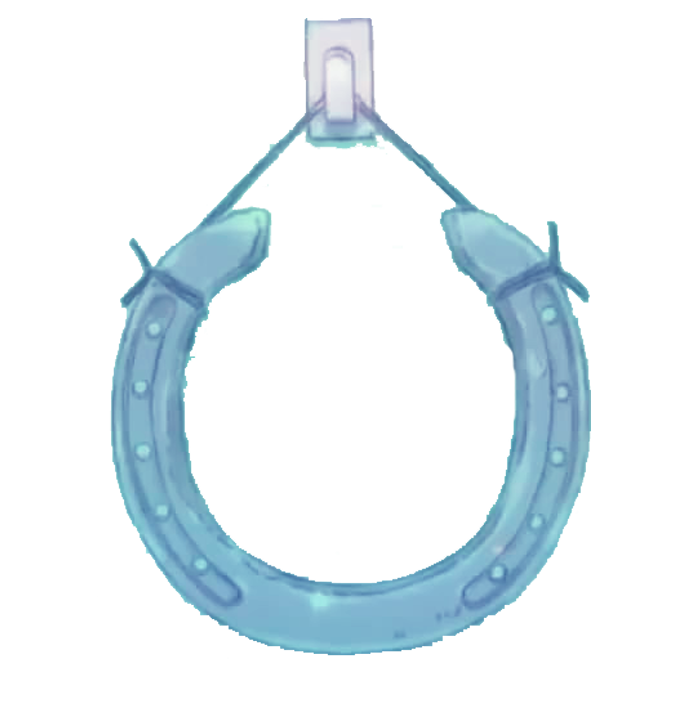情与义
在波士顿花了两年时间爬完了马斯洛温饱与安全的两层金字塔,在北京却像空气一样自然。此前谈爱过于奢侈,如今却可以在第三第四层爱与尊重上仔细讨论。上一篇文章情与利 虽点出“交情”亦是利的一部分,但其与真情的差异仍是一眼可辨的。这篇文章便来谈谈更为精细的情与义之间的差异。
首先此处的义并非指孟子的义,而是源自于某个朋友看完《繁花》后抄来的“A自称有情无义,而说B有义无情”。当然下一句便是B说A怎么在骂人,说明当事人即使这么做,嘴上还是不接受的。在那场戏的语境下,有情无义指的是暗送秋波而不敢/愿行动,有义无情指的是尽到应尽的责任也绝不过分承诺。当然镜头一转便可知其原因是穷小子被投奔利益的爱人伤到,放话十年后让她后悔,由此成功或者说利变成了最终目的,剩下能做的最多称之为义,而说不上情。
空一句有义无情,和加上后续的情节补充,给我的体会便大有差异。我的确更能理解后者的做法,以以往我从“指向他人”转向“指向自己”的视角,先使用一切他人可接受的方式攫取与积攒自己的利益,再与他人沟通与接触。只可惜常规的故事中往往只有前一步,便在追求利益中迷失,再也回不到“指向他人”,或者说重获爱的能力了。不过我还并未看完《繁花》,或许对上述话题有进一步的情节阐释。
从“指向自己”到能正面回答“爱真的高于一切吗?”,着实并非一蹴而就。一来事业须有受挫,但又不是不可逆的低谷,二来期间并未放纵,而是转向追寻所爱的替代并不断得到正反馈,由此才能建立起事业有成时仍能或者更能把爱当作终极目的的正反馈,而非把事业当作最终的寄托。除了浮士德般的造大坝,少有事业是以指向他人而获得或幸福的,单纯指向自我的事业可以作为幸福的最低保障,但孤独中不会酝酿出理想的生活。
对最后一句,不妨提及昨天我在《海子评传》中读到的惊讶事件:海子作为教师兼诗人,在京郊的昌平竟也是孤独到主动想去酒馆念诗换酒的,没想到老板说送酒喝可以,但不要念诗。这一滑稽的故事真的直插孤独的心脏,精神与物质的世界看似以诗与酒产生连接,事实上酒不过是现实世界的道具。这更坚定了我碰杯喝水的想法,与此同时寻觅能随意念诗的环境。
更有趣的是,海子的生活中也出现了上文的穷小子困局,他并未走向世俗的成功,而是把诗歌写在了各省的大地上,至于最终为何导向自杀的结局,也还需要我更仔细的品鉴与体会。
两种不同渠道看到的穷小子困局,让我不禁怀疑是否因为文学滤镜导致了现实细节的失真。因为于我自身而言,所遇的情况似乎更为复杂,我也曾自卑于出手拘谨,以至于有收入后带有点报复性意味的随意消费。我也因所爱的人而心碎,但往往是在细节中意识到对方并非我想象的那般看重这爱。经济上的自卑与爱情上的受挫却只是两条平行线,没有在交汇的瞬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第二容器末尾它们接踵而至,使得我开启专注于利的生活,但于我而言仍旧是两个分离的课题。
对此我试图的解释是,一是时代不同,上述的穷小子困局都发生在八九十年代,一个选择真的能有跨越阶级的作用,相比而言爱情的表露与需求也更加隐晦,一个眼神便足够回味许久。如今似乎兜兜转转还能碰头,来自社会的巨大诱惑和极力阻碍也减少许多,更多的情境下两个人只需面对自己内心的选择,人也无法用社会大潮这种话来安慰自己,重利就是重利,不爱就是不爱。二是我的家庭确实在我经济独立前给了许多经济与爱的支撑,当然并非能说足够,否则我也不必如今仍把解决家庭问题作为课题之一。坦白说,我确实有被刺痛过的时刻,其巅峰大概便是本科新生舞会找舞伴与挑选着装时遭受的或许中肯但不留情面的评价吧。我虽能以不屑的态度面对波士顿新生舞会,直言我并不需要这种社交方式,但到彻底无所谓到可去可不去,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写这些时我猜想自己绝对还有些被深埋的自卑记忆,未来会以情结与强迫式活动的形式出现,不过到时候记得见招拆招就好。
其实话题有点偏离了,拉回正题。情与义的问题在被朋友提出时似乎是独立于利的,但于我而言仍是情与利问题的变种,即一端是情(指向他人),一端是利(指向自己),而中间表面上为他人好,实际上为了自己舒坦的样态,与上文提及的义更为接近。至少《繁花》中给我的体会大多如此。当然此处有另一个维度,便是是否敢于直面自己所求。不敢面对时,便会延伸出有情无义和有义无情的说法。这一模型倒是比此前我以数学模型提及的“情义利三者两两线性无关,但三者线性相关”更为贴切,即动情、逐利、有情无义和有义无情分别在情与利维度与直面所求维度划分出的四个象限中。当然这些都只是自娱自乐的数学模型,是现实情境的简单分类。不过如何构建模型能够影响自我看待失误的角度,根据同一事件给出不同侧重的描述。
我注重且一再强调直面自己诉求的说法,一来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直接相关,二来我自己着实花了许许多多年才积聚直面的勇气,而且是在不断自我考问与他人助力的情况下,所以我粗糙得以己度人地认为这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个还未解决甚至从未面对的课题,并把此作为了解人性的基本假设。
基本假设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我的另一课题便是探求人性的基本公理,然后便可以暂时不再追问甚至生气,而持有宽容的态度。不得不说最近对ZFC数学公理体系的了解着实大幅度影响了我的人性观。比如如今粗糙提出与使用的几个公理是
1)马斯洛需求金字塔:温饱、安全、爱与归属、尊重、自我实现。
2)康德:人的理性有界限,但理性可以设立与明确界限。
3)弗洛伊德:人有潜意识,与意识共同影响活动。
4)海德格尔:人有必然的沉沦倾向。
5)海德格尔&萨特:人需要与他人共同存在。
当然上述几条不过是我从哲学家那儿摘抄来的一些说法,如何使用它们并推出一系列的论断则是哲学意义上我需要做的。提出这些公理并非像斯宾诺莎伦理学那般推而广之让他人接受,而是让我能够更好的理解他人的活动。比如第一条和第四条便能让我理解与接受为何经济独立、原生家庭、爱情经历是所有人都能说上几句的话题。而第二条和第三条则能让我明白人的知、言、行有根本性的分离倾向,需要外力的作用才能结合到一起。第五条也能让我承认孤独并非值得追求与沉浸的状态。
回到情利与直面的二维模型,由于我可以对“爱真的高于一切吗?”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坦然而直接的回答,我如今是站在情与勇敢的象限去审视其他三个象限的。对于逐利,我理解、接受,甚至偶尔还能欣赏ta的能力,但最终只能祝ta好运。对于有情无义和有义无情,或不敢直面自己所想的人,我原先肯定是以更为苛刻的态度抨击,如今我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直到无所谓。
但前提是,处于其他象限的人不来侵入我的世界,或者我预先能切换成对应的营业模式与之接触。去年此时我了解到friends with benefits的说法并为此耿耿于怀,甚至怀疑我与某些朋友的关系确实如此。当事人确实否认了,甚至在其理解范围内尽力了,但我最终明白我追求的爱对方给不了,并在另一些经历中充盈了心中被爱与爱人的能力,便不再要求他人实现做不到的事了。我会试图先观察对方的偏好或者说能/愿意给出来的东西,再看这个东西能否与我对真情的诉求相合,或者次一级的能否对双方都产生实际的利益,然后再决定我的行动与我对对方的态度。至少目前我自信是能够在情上提供足够的支撑的,只是对方能否承载得起这份支撑,或者是否需要这份支撑。在对方想我的时候恰好想ta,在我看来才是促成真情的方式,虽然事实上我多多少少持续不断地想着ta,只是主动压低了幅度而已。
不过在第一阶段,我倒是逐渐明确某种让我不舒服的对话方式,便是将利包装成情来劝说。其中一种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替人说话,比如A与B和C都是朋友,B和C虽是朋友但B自认为不如C,当A与B讨论时,B引用认知滤镜中理想的C来压制、反驳、诱导、劝说A。更一般的情形是C是社会,A着实无法辩驳,最多只能不接受。而当C是某个具体的、A熟识甚至称得上是朋友的人,那么B滤镜中的C和A眼中的C便会产生落差,甚至会让A产生C要是在场也会对B捧臭脚的模样感到无语的想象。这种互动方式在我看来也属于广义的八卦,因为也是借用他人名号压人一头,实际上躲藏在后面传达自己的想法。此前我作为A应对的方式当然是先了解C,或者向C求证,再回头试图纠正B,而如果抽象成上述模型,便不难看出,如此做法不过是A与B互换罢了,B一来也会不适,二来最多也是向C以滤镜的方式求证。直到我意识到三人间的两两关系和三人共同在场的关系并不相同,才萌发出把ABC放在同一环境,但作为A主动挑出此前与B关于C的态度,让C可以采取直接的行动,由此才可在A与B单独接触的情境下发生变化。而如果B对C的滤镜十分浓重,那上述方式只能产生量变,我还未摸索出产生质变的方式,只能暂时强行屏蔽所有B眼中理想化的C而直接与不完整的B和平共处,同时在另一情境下与C接触。
上述中的B与C有几个具体的样例,分别对应我未解决或应面对的几个课题。如家庭情境中的B为我爸,C为美国。当然还有三人组朋友以及多人合作的情形。有些陌生人在试图成为朋友的第一次交谈中,便化用了作为社会的C,那便会被我归于广义八卦的团体而强制“原谅” 了。于我而言,可能值得交往的是躲在C背后的B,至于C,我自然可以在别的情境下与之接触。
如此并案处理的优点便是,一旦我能够解决家庭中的课题,其他情形更多地像是推论。但缺点也是我容易掉入与最困难的问题对峙的深渊,而有时在其他简单情境下磨炼出的技术做推广才是解决问题的巧妙道路。只是这都很难讲,我也不过是抱着搞科研的心态面对我遇到的每个大课题罢了。在方法论上的重新考量也是需要注意的,所以我也试图学习与了解艺术性的心态与行为方式。
12:21 2024年12月7日
追寻爱情时把理性解决问题当余兴节目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