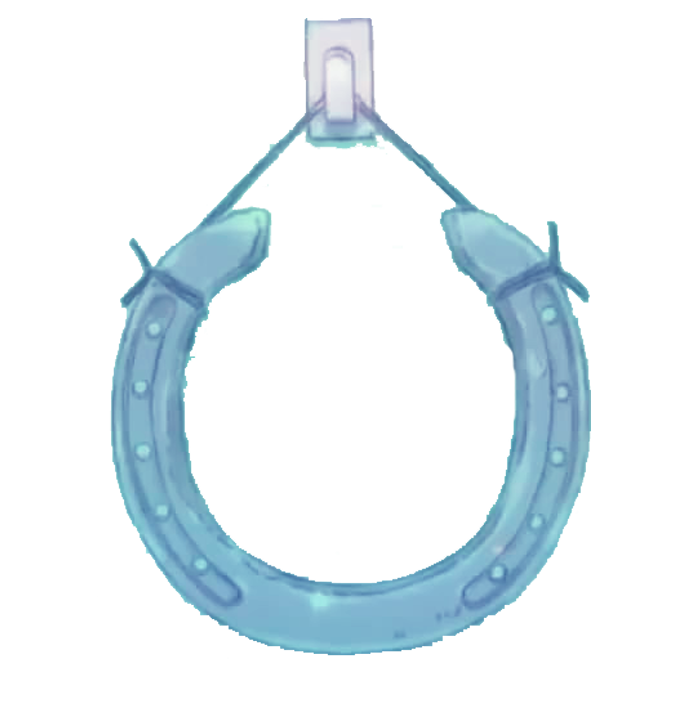爱与真正想要的
今年的生日文迟到了。10日晚上11点时吃了个橘子便开始腹痛,一觉之后并未好转,生日当天受《海子评传》启发和朋友到昌平走了一遭,晚上重探了一回北京最有设计感的洗浴中心,在卡拉卡拉倒闭后又找到一处灵魂的避难所。可腹痛在温暖散去后又会持续,12日去医院做了基础的检查也毫无大病,只靠着些肠胃炎的药当作安慰剂。
我把腹痛归结于情绪所致,此前紧张会在脑中叮的一声导致腹泻,而此次腹痛则源自于恐惧,而且是理性已经觉察到后仍然弥散在理性之外的恐惧,即逻辑分析没啥可怕的,我也自信能够应付,甚至我也以向朋友倾诉的方式分析自己的状态。然而身体,尤其是肠道,能接收到恐惧未消散的信号,并通过身体的症状让理性的我感受到。
弥散性的恐惧难以处理的点在于,具体的事件只是诱因,而对恐惧本身的恐惧才是层层叠加的。况且对具体事件的应对方式理性也完全能做出谋划,我便借着身体隐痛的时刻,来写点带点伤痛的文字吧。
去年的生日文 帮我理清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让我如今不必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当然卸下的担子也只是近十年的,去年留下的问题就直指十年前的对爱的追寻,这一年来着实在此之上迈出了许多歩,我不仅可以自称明白爱生发的契机,还可以对爱的发展、转变、消失等环节展开谈谈自己的感受与想法,当然自然会隐去当事人。甚至去年纠结的问题,我是否被他人爱过,也有了坚定的回答。或者说,我自认为自己多少在被爱和爱人的能力上有些提升,也庆幸这些提升来自于与契合的人(们)的共同探索,而非以过往心动心碎的痛苦循环来加深内心的犹疑。除了无疾而终,我用一个新词“平稳落地”来描述爱的长远发展,使得对最终能拥有以及长期拥有的可能性也抱有了正向的期待。
六月份与十一月时各被问到对爱的看法和真正想要的东西,后一次时以较为轻松的语气描述,而前一次时的严肃表述于我而言更为精准,虽然现在写下的表述也只是对当时的回溯。我大致记得自己说过,我探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上限。上限这一说法当然来自某人提及的95%往上每一步都会很艰难,而我会拼尽全力在97%之上追求98%,而只把80%的关系当作余兴节目。“余兴节目”这个词也是最近我常用的,似乎带有点轻蔑,但着实能够点出我有兴趣但并未投入,且当机会出现时需要随时被让步的心态。我也学会更轻松自然地拒绝他人出于情谊的邀请,如果我认为双方对同一活动的情感期待没有大致拉平。这种心情来自于八月被问最想要的是什么,答亲密关系,而得到同学情谊也被归结于亲密关系的令人哭笑不得的回应。这种滑坡感让我越发觉得在95%面前,90%的亲密度也会黯然失色,而平稳落地指的便是曾向上探到98%,而平滑降落到到85%并保留向上的可能性。
近来实际上是以积蓄能量,以余兴节目为未来新的上限做准备的时期。靠着平稳落地的感情,让我不至于在波士顿一般时刻要在孤独与挣扎间做抉择。我的恐惧大概也来自于余兴节目这一心态。因为我已认为与许多朋友的交往不可能突破98%的上限,原则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掏出淡如水的武器在相聚时畅聊,而又毫无顾忌的离开,但我又有种我对对方很重要的错觉,并也认为我的存在确实能影响与改变对方,于是交往不再是出于爱,可能还有些许感情,但又夹杂了责任,也有些余兴的兴趣。对于老练的社会人,我想这种模棱两可情利交织的关系是常态和善于处理的,但我一不想像社会人靠拢,二也不知如何应对这种状态。只关注利的资源交换反倒是让我轻松的,让我进退两难的是我在寻求维系情,说出的话和对应的行为则像是获取利,可实际上我又不怎么需要这些利,可这或许又是对方能给我的ta最好的东西以及对方表达情的方式。我明白我所求的东西,也确实在追求的道路上前进,可我又还在闲暇之时被动享受到另一个世界的照顾,当然也有以“润物细无声”的影响。
今年的我已经对去年遗留下的“对理论与现实的划分有明确的表述”感到迷惑,仿佛已经不明白以前纠结的点究竟在何处。我当然可以这与上述讨论的余兴节目和恐惧相关联,但又觉得似乎是两个问题。恐怕这个问题还得继续滚动交给未来的我。
而对去年生日文中解决家庭关系的愿望,我在一月、五月、八月,和前几天都有所尝试,可以说也有长足的进步,我当然可以预计明年今日这一问题已然解决,但如今我也只能认为是有阶段性变化。以我今天和朋友闲谈时提到的,与家人之间的独立(至少)有三个阶段,经济独立、情感独立、决策独立,三者层层递进,也是我解决家庭关系的顺序。经济独立指的是每个家庭成员虽然可以互通有无,但一定要自负盈亏。情感独立指的是我需要在家庭之外建立灵魂安放之处,借助朋友或者享受自我来消化情感的困难,而决策独立指的是在大事上自己拿主意自己担责任。如今我相较于父母是独立的,但父母之间却没有达成独立性。当然作为伴侣,彻底的独立那不如分开,所以独立更多指的是“能够”独立,而非“一定要”独立,能不能、想不想、要不要在这里又成了重要的差异模型。我认为明年今日能够解决的原因是,我近来通过与朋友的交谈收获了一个很好的走出困局、发挥家庭中每个成员优势的方式,只是有待实验与时间检验。至少三个人在情感上和逻辑上都不至于抵触,只差具体去做了。
对于找到“更多”真正想做的事,六月时是个让我迷茫而无所适从的课题,而以与朋友交谈后立志成为“波士顿的王”而又在波士顿算不上是灰溜溜而是自由而主动地归来,让我已然自信能够成为“梦想收集师”。在波士顿的职业交流活动中得知有个职业是生命教练(life coach),但我仍更喜欢我自己的说法和方式,因为后者更像个付费私教,以服务他人成就自己的角度出发,“梦想收集师”指的是寻求和聆听他人发自真心的梦想,不强求帮助其实现,但会记在心里作为未来“上身”时的角色之一,即以“我真的有个朋友”开头,与新接触的人碰撞出单纯的自我梦想接触不到的侧面,如果恰好有幸认为能够一拍即合,那促成双方认识也是不错的选择。但不强求牵线,一来此前有许多强行牵线造成尴尬的经历,二来作为中间人还能当个“梦想翻译家”。不过总得而言,“梦想收集师”是也是排在“真正想要的爱”后的余兴节目,甚至此前让我恐惧的情利纠缠的交往中,也有寄托着收集到梦想的愿望。它的确更像个职业,而且是我数学科研外的副业,在闲暇时间纯凭兴趣行动,兴尽或者能量低时便收敛触角回到主业甚至是寻求爱的世界中。其实以这个心态出发去真诚地展现自我,是不会让我恐惧的,只是此前疲惫时随意地采取了逢场作戏的姿态,让我产生了落入社会人圈子被吞噬的恐惧吧。如去年的生日文提及,人类学方法与视角着实是个很好的屏障,让我在心态上即可以放开来与“社会人”打成一片甚至尝试共情,又在学术或者态度上保持随时抽离的研究性视角。至于进一步的平衡和场合的选取,还有课题和梦想收集的偏好,则是可以之后详细讨论的。
所以似乎去年的长期期望都已然有了进展,并且都能在可见的未来退居二线。对于短期期望,一是资本论完全搁置,短时期也没想着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二是人类学方法已经“实装”,三是对诗歌的探索还刚从《海子评传》与昌平漫步开始,四是意料之外的在五月完成了一篇插叙式的论文,长久以来导致痛苦与恐惧的大工作也几近有初稿,虽然我实际认为这个工作才是腹痛的恐惧源头。所以客观来讲我已经能算是“二段少年”,甚至写完这一大工作就能在自我评价中升“三段”了。但正如“棋魂”没有再讲初段少年后的故事,我与波士顿的故事也终结在了“逃离三边坡”。更有趣的是,曾经对菲尔兹奖的执念以两件滑稽的事走向了终结,一是某国安国产剧里某一泄露文件的数学家声称“没想到外面的诱惑这么大”,结果下一幕国安人员闲聊时说“对方承诺给菲尔兹奖提名”。只能感叹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承诺”“提名”真的太太太典型而讽刺了,便值得称得上“巨大的诱惑”。于是我还是把执念对象转为了佩雷尔曼和萨特。二是曾有种菲尔兹奖能横着走,改造(国内)数学界的拙劣想象,没想到菲尔兹奖也有屈服于菲尔兹奖的滑稽戏,皇帝也可以变成尊者。就转而吃瓜看戏,好奇一出好戏如何落幕了。幸运的是,数学已不再是我最后的避难所,大概只是倒数第二个吧。
对于未来,除了上述几个问题的收尾外,或许还一个值得一提的便是对第三空间或者叫公共空间的营造吧。这当然也是历经十年的问题,感谢凤凰折纸社,感谢泛心桥数风事务所(PHMO),感谢卡拉卡拉,或者也可以感谢波士顿不读书的读书会。我需要仔细筹划公共空间的构建,让我与我所爱和爱我的人在灵魂飘荡之时有个去处。
22:13 2024年12月13日
还是有点腹痛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