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后闲想总集(更新《存在与虚无》)
这一年毋庸置疑是“独立”落地的一年,去年12月31日厘清旧账走向经济独立开始,各方面独立的进程如洪流般启动。春节、五月初、7-9月与家人和亲戚的互动让我从家庭中独立;春节后与旧时挚友(们)的袒露,以及此后几次举重若轻的会面,让我从过往的感情中独立;4月火车环游美国的旅途,和5-11月的北京定居,让我甚至从“自由的枷锁”中独立;近两月的实验室组建与单人写论文,让我挣扎三年的“学术独立”也看到了可能性的曙光。
没想到虚无又一次地找上门来了,这次不再是身边朋友的访客,至少有一道隔离的屏障,而是光明正大地坐在了客厅的中央。在虚无释放它的气息时,我的工具箱中已有不少应对的方式,可无穷大的虚无需要一个无穷大的容器才能装下,现有的工具,或者梦想,最大的特点是它们是有限的,也就是随时可以被“虚无化”而“搁置”的。
自从在工作待遇上习得谈判心态后,我潜意识地将其迁移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处事是与他人谈判,规划是与(未来的)自己谈判。此处的谈判,指的是在明确自己所需的利益、能让渡的利益、拥有的筹码后,尽可能通过有来有回的沟通拉扯中让事情往自己希望而对方也接受甚至满意的方向发展。
过去破碎的自己似乎又被慢慢拼起来了,虽然还在等待风干一碰又碎,但胶水还在花些时间总还能粘起来。不如说因为我找到了生活的胶水——安心感,所以允许自己反复破裂塑形,调整至自己最为舒适的状态。
父母在北京的暑假以推迟六年的毕业典礼为“峰”,以围观九三阅兵为“终”。我探索出与父母最理想的相处方式是住得近而不住一起,过往不自觉的紧张压力状态被觉察与缓解,虽然还带点胀气的尾巴,却也是可以接受与应对的了。父母的生活与愿望被交由他们自己负责与实现,我不再需要背负额外不必的重担,可以堂而皇之地只关注自己的感受,以及选择自己面对世界中的别的他人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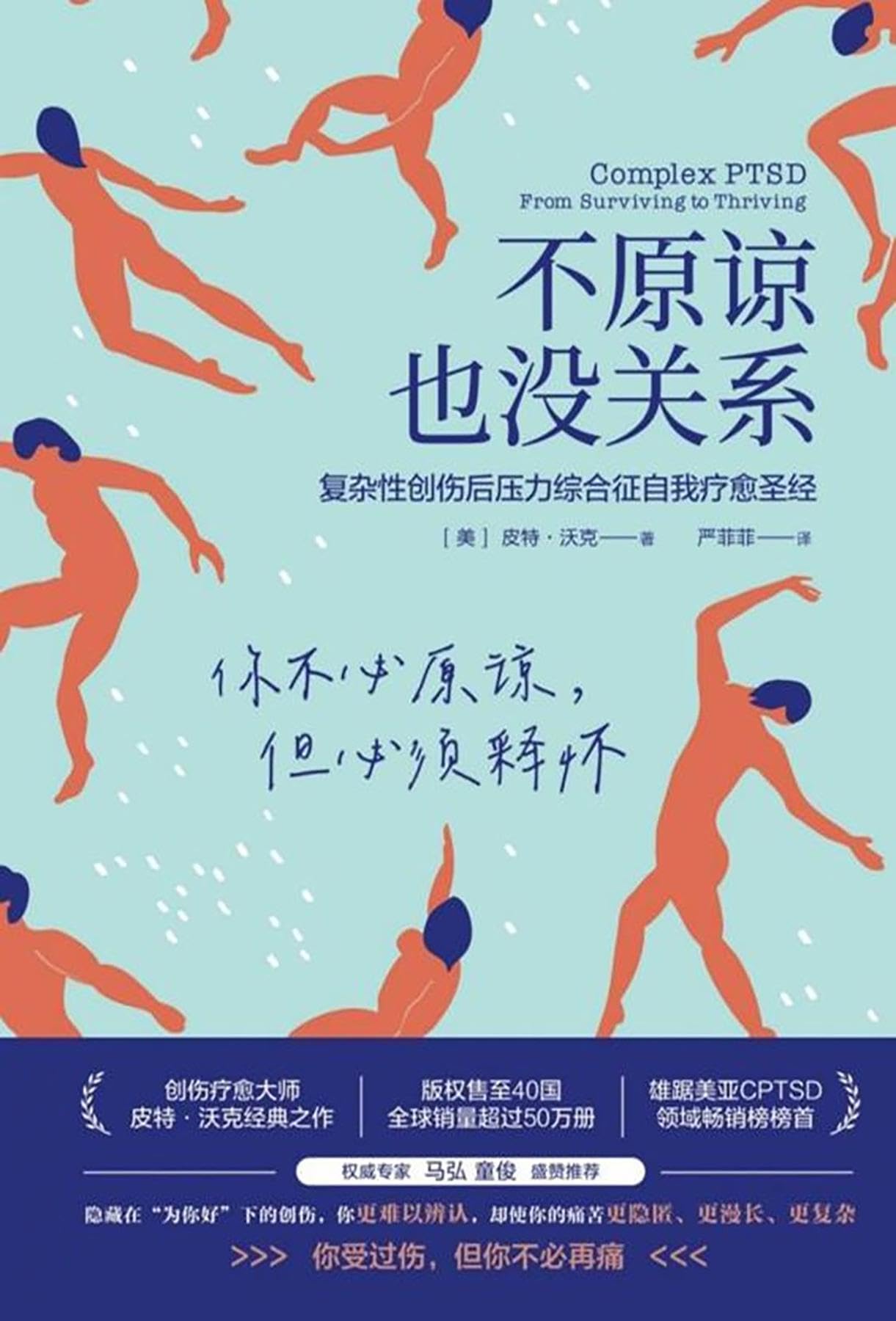
哲学能让人理解痛苦,而要在实操层面面对与处理痛苦或许还需要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辅助。在此时隔两年重启“书后闲想”系列而非继续写随笔,是因为我自认所面对的困境以无法用理性抽象的方式软化与应对,数次与朋友倾诉时受挫后也丧失了表达的欲望,最终选择了靠自己硬抗。借着书讨论至少有个依托和锚点,在兴趣层面做些抒发,也可以点到为止。
自从接受了隔阂的存在,许多沟通便能轻而易举地点到为止了。而自从承认了许多标签化的叙事,许多事情确实变得简单而令自己舒服了。从与世界全方位的抗争,到积蓄力量定点击破,我在允许自己被世界改变的同时试图拓展自己活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