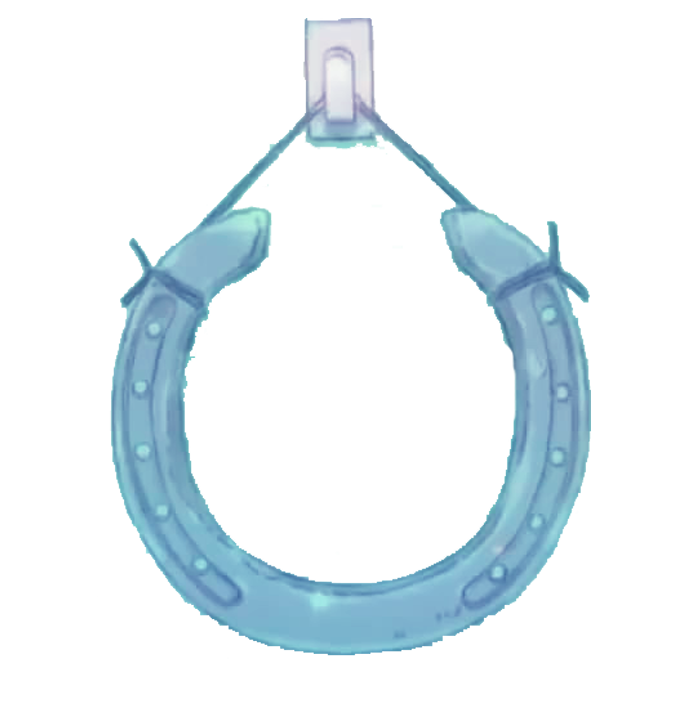重新拾起的闲想‖《第一哲学沉思集》&《理想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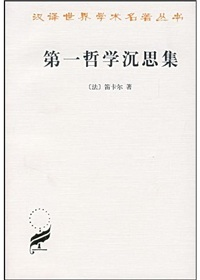
未曾想,2016年最后一篇“书后闲想”竟是五个月前之作。这个学期,主要的工作在于输入而非输出,一是因为调低了优先级,二是因为心境上“入世”较深,反倒没有闲心观察自己内在的想法了。
阅读虽有所缩减,但的确是在继续的。因为所选的几门哲学课程都与文本有关,于是看得书也都是课程相关,但并非“教科书”,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便是一例,大体的流程是自行阅读、上课讲授、讨论课进一步探究,当然还有最后期末的复习整理(其实是在论文的督促下)。这一趟下来,的确是比此前单独快速阅读过一本书体会得要深吧,像这两本书,在我第一遍读的时候,也是云里雾里,只能捡到零星的思想残迹而无法领略整体的架构。此前的“书后闲想”大多也只是根据这些残迹,结合我自己联想到的、自认为对自己有益的想法来谈的,而到了正经阅读之时,反倒不敢把类似的联想写下了(或是外扬)因为大多都只是不成熟的想法,发散性虽强但连讨论课的台面都上不了吧。当然两种阅读方法必然各有优劣,精读文本的方式更能建立我对作者整体思想的理解,反倒有时刻意遏制了自己的想法,因为没有文本依据的想法在我看来大多是自己的瞎扯,本就不必寄希望于他人的认同。而哲学的探讨必然是建立在交流上的,所以对于交流的规则,还是需要达成依从文本的共识的。
扯了这么多闲话,其实是有些畏惧久不肆意带来的生疏感吧,这学期写了若干篇论文,但鲜有随心之作,大多都有“憋”的意味,没有那种兴来起笔,兴尽便点到为止的酣畅感,于是有些担忧目前写下的文字,是否依旧会有些显得谨小慎微?对两本书文本的概述以及思想总结就省略了,这是考试要准备的内容。越俎代庖难免演变成班门弄斧,所以依旧照着以前的画风,单挑我想到的部分讲吧。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先谈《第一哲学沉思集》吧,自以为了解得更全面一些(因为文本短)。阅读此书前,对笛卡尔的了解可以用几个短语概括:解析几何、数学+哲学家、我思故我在。是的,仅此而已了。我对有数学背景的哲学家(或者叫有哲学背景的数学家?)有一种认同感,毕竟这两者我都比较熟悉和喜爱嘛。此前有些迷罗素,主要是因为他提出的悖论,不过在他写的哲学史被批了一通后暂且“悬搁了我的判断”(特意引起来是因为这梗在《沉思集》中出现了)。回到笛卡尔,第一遍浏览这本书时,我还是有些惊讶于笛卡尔也是一个讨论上帝话题的人的,必须承认自己一瞬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毕竟“上帝”这个词附加了一些宗教的含义,但此前粗浅地了解过斯宾诺莎泛神论中的上帝观,对这个词的态度稍有转变,便耐着性子往下读。
第一遍当然是被绕得云里雾里的,虽然笛卡尔的数学背景让他的行文逻辑相比《理想国》(后面再说)更有条理,看着也更加明白,但时常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时,我才忽地反应过来他已经论证完了。“上帝不是个骗子”“凡是我认识得清楚明白的东西肯定是真的”这般的结论都先暂且接受,啃完了第一遍(这本书只有一百来页啊),要是就此打住然后开始写书后闲想,估计我能拎出来的要点只有普遍怀疑和模模糊糊的我思即我在吧,然后批驳一下笛卡尔给上帝赋予了太多的性质,以至于论证顺风顺水就完事了。当然现在的观感肯定不会如此了,正课和讨论课还有额外的问答算是能够让我搞清楚笛卡尔想解决的问题、成功论证的部分以及不完善的论证部分,笛卡尔也从“面目可憎”的开口就要谈上帝的形象变成了一同在哲学道路上奋斗的先驱。
我思即我在
精读文本的优势在于化解误解,第一大误解即是广为传播的“我思故我在”吧。我思并非我在的原因,“我”就是作为一个“思想体”而存在。“思”的一种具体表现是第一沉思中的“普遍怀疑”,故也有讹传为“我疑故我在”的版本。而在文本中,则是认为在“我没被骗”和“我被骗(所感受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的)”时,都有一个“我”存在,前者不必提,后者中的“我”是那个被骗的我,而非思考的“我”被骗的“我”,因为连被骗的想法可能本身也是外来的东西塞进来的。笛卡尔还特意强调这个“我”并不在时间上连续,一旦“我”停止思考,就无法保证“我”的存在。故“我思我在”是一个非常弱的结论,但又是一个从无中抓出一个有的关键性结论。
“我思故我在”并非出自笛卡尔本人,应是传播中产生的误解。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人的思想被高度总结(无论是别人总结还是自己总结),因总结后的文本表意的局限性,容易让人产生违背本意或是断章取义的理解,若是以此粗浅的理解转而批驳思想的源头(一般是在日常交流中作为例子),则是十分不妥当的。与此相近的还有“存天理,灭人欲”(人欲是指过分的欲望而非基本欲望)与《庄子》中的“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惠子的想法而非庄子的),各有吹黑。所以此前我也强调,尽量在不了解、单纯听到一个浓缩思想之时,不作过多的褒贬判断吧。
洗濯上帝的概念
虽然写的顺序是书中论证的顺序(普遍怀疑→我在→上帝在→真理规则→物质本性存在→物质存在),但我不准备再挨个阐述书中的思想了,一是因为我的概括很可能也只是一种理解(而且是在我上完课、被老师影响之后的理解),二是一条条按逻辑线列出,就太像中规中矩的论文了。不过上帝这个话题是必然绕不过去的,因为副标题中便有论证上帝存在的意思。
此前提到上帝被赋予了太多宗教含义,导致我初读有一种自然地抵触,我想这是语词被含义“污染”的一大例子。当我们用一个已有的词来为一个后来的概念命名时,给人观感时,必然与此前的概念产生混合,这是文本传播时的一大弊病。包括此前的“骗”,我特意用括号注明,也是因为此前在讨论当中刻意消除了上帝“骗”我的道德性内涵而是特指上帝让我接受的外物与外物本身不一样,虽然自己能够明白,但在讨论当中也得时时刻刻强调这一点,避免双方用同一个词表达不同的含义,使得讨论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于是有一些哲学家选择造新词(没错我说的是海某某尔)来消除这种状况,但这又会带来一个问题:接受者无法对此直观把握,只能不断通过描述的界定来使得这个词的含义得以彰显。在这种情况下,最怕的是创造词的本人都没想明白,空对空的大谈,发现什么都没有说(对哲学家来说这倒不会发生)。
所以得先把上帝这个词洗干净(好糟糕的感觉,当然借助原有的词必然会有含义的残留),然后讨论上帝的存在性。但笛卡尔上来先把“上帝”这个词在浑水里漂了一波:
用上帝这个名称,我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第三沉思)
当时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真想冲到笛卡尔面前扇他两个耳刮子,因为此前他塑造的谨慎求实的形象瞬间变成了上帝的死忠粉的样子。要知道一粉顶十黑啊,笛卡尔先生能不能在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先把自己的口水擦擦……orz
这就相当于原先笛卡尔领着你在一个迷宫里走,此前遇到的岔路显然都是不怎么靠谱的,遇到的障碍他也能轻松化解,你也挺信任这个导游的,但到了这儿,迷宫的关键部分,你的面前忽然摆出了一二三四五若干个无法分辨的岔路,而你还在张望时,你的导游早就不知道从某一条路里偷偷溜走了,只听得远方的笛卡尔叫唤着:快来啊我在这儿发现了上帝存在!但你还在岔路那儿一脸懵逼。
好了不打奇怪的比喻了,说正经的。书还是得继续看下去,遇到问题再折回来咯。洗概念的工作交给了读者,精读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也是在讨论上帝的定义,若干弯路暂且不谈,最后大概是洗掉只剩“无限的实体”这个概念属于上帝,也就是笛卡尔在论证当中只用了上帝的无限性这一性质。当然这是授课的老师给出的理解,根据我自己的漂洗,却似乎发现“至上完满性”好像也去不掉。当然“无限性”意味着什么本身似乎也有待商榷,我给出的一种理解是无限性包含至上完满性,这样姑且能跟着老师这个新来的导游走,但最尴尬的是走过几个沉思之后,忽然又说至上完满性在第五沉思上帝存在的第二个证明才给出,于是我感到自己又陷入了迷局,连忙低头看笛卡尔的脚印,发现笛卡尔根本没提这事,而且至上完满性也的确早早地融入了上帝的定义。最终我发现,笛卡尔走通了迷宫,老师似乎也走通了迷宫,而我却被绕进去了,因为我觉得两条路都有破墙而过的部分,但在破墙的时机不一样且途中有交叉点,所以稀里糊涂的通过交叉点换路走是能走通的,但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脱离文本单一谈我的迷惑似乎容易让读这篇文章的人也陷入迷茫,还是终止这个话题吧。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哲学文本中这种多条路的情况,作者可能选择了一条路走通了,可能压根没有走通却以为自己走通了,但是他在描述自己走的路时,给出了许多迷惑性的路径,虽然有一部分能够殊途同归,但也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死路。而后来的研究者要么空降到路的中央开始走,要么从头选择了一种自己的路走,为了证明自己的路是对的,及其容易给其他路径都打上“道路不通,请放弃”的标志,若是自己能够走通,倒也好说,不管是否和作者思路相同,至少是一条新路,但万一自己也在某处使用了穿墙术,而且隐秘到自己也很难发现,那就有些尴尬了,很可能一次穿墙后就停不下来,最后根本没到迷宫的出口,反倒硬生生凿出了新的出口。(郭象以《庄子》内外杂均为庄子本人所作的前提来注庄子)至于那些空降的研究者,则是会陷入如“笛卡尔循环”的误解当中,永远在兜圈子,不过出现循环,还得怪笛卡尔写出那么多条岔路啊!当时把口水擦一擦直接说上帝=无限的实体不就完事了么!其实,笛卡尔还真作死把自己的论证以几何学的形式(也就是公理化)写出来了,里面明明白白写着:
我们理解为至上完满的、我们不能领会其中有任何包含着什么缺点或对完满性有限制的东西的那种实体就叫做上帝(第二组答辩后附)
只可惜,上文说了,按照这条路子,也难免会用上穿墙术才能走通,只是笛卡尔不自知罢了。不然后人也不会找各种新路来试图走通了。而且尴尬的一点是,所谓的“路”也不过是后人的归纳总结,由于语言传播信息的局限性,很有可能有些路并没有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而读得越多、越细,找到新路(不是指贯通的路,而是指两个结论之间的论证依据)的可能性更大,《第一哲学沉思集》有一个优点便是附带了若干组答辩,也就是说,有许多当时的探路者向笛卡尔提出了质疑,笛卡尔也相应地给出了解答,这可谓是宝贵的一手资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此前的循环便是答辩中消解掉的)不过坦白地讲,我只是粗略地扫了一遍,就像我第一次看《第一哲学沉思集》那样,那些文字在我心中依旧不过是若隐若现的关联。而且因为客观(期末)与主观(我懒得再细究)的原因,我也并没有沉下心来在文字中慢慢探索(这更多的是研究者的工作),虽有遗憾,但也便止于此吧。
沉思体相关
虽说笛卡尔的文本有种种可见不可见的不完善性,但他的行文是我非常喜欢的,清晰而注重逻辑(除了部分因为流口水带来的失误外,当然这个失误是很麻烦的失误),从外在的生活体验逐步抽离(普遍怀疑),转向内在的哲学思考,再一层层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中途不免有所收获的欣喜之感。可能我希望追求的也是相近的思想体验吧,不过笛卡尔自己也说,这种沉思一生也不过只有一次,而且是要在思想足够成熟之时才适合展开,这便与我现在写的“书后闲想”有所差别了。我更趋向的是他在《谈谈方法》中叙述的方式,开篇阐明“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方法”,整体的架构也都是开放而富有见解的,第一次阅读时更为友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看《第一哲学沉思集》几乎想把笛卡尔和上帝从窗外丢出去,而看《谈谈方法》则转而喜欢上笛卡尔了。不过后者先于前者,也有部分前者的思想(如普遍怀疑、我在与上帝存在的证明),当然也有有所改进,一为轻松闲谈之作,一为严谨的集大成作,我想还是在阅读态度上有所区分。
柏拉图《理想国》
如果说《第一哲学沉思集》是“小径分叉的花园”,那么《理想国》则是牛头人(弥诺陶洛斯)的巨型迷宫。而且这学期是先看后者再看前者,以及后者的对话体传达信息清晰度远低于前者的沉思体,可见给人带来的心理阴影面积。即使到了最后,我也不过是在老师的指点下,断断续续地摸清了些许主干线,至于柏拉图原本希望走的路,则是隐匿于迷雾当中了,倒是给后来的学者很大的发挥空间。
逻辑上最让我诟病的是苏格拉底话语中常用的推理方法:A属于C,B属于C,故A等同于B。这根笛卡尔摆出上帝的若干条性质一样令人在意,尤其是苏格拉底时常用这个逻辑推出一些关键性的结论。类似的逻辑得到的推论有哲学家(A)是正义的(C),正义的人(B)的生活是正义的(C),故哲学家(A)等同于正义的人(B),哲学家的生活幸福,故正义的人生活也是幸福的。对此,和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类似,有种可以预见的解释:这段表述不过是不充分的回答(像《沉思集》中的最早出现的上帝不会骗我),后文有更精确的论述补充。这其实是建立在否定文本的基础上,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乱凿出口),但在对话体中可能运用起来更顺畅一些,因为苏格拉底的语言中的确有循循善诱的意思在。还有一种解释是直接否定我提出的例子,像“我思即我在”一样给出另一种合理的解释且符合文本,这倒是我希望得到的回应,因为正如上文所说,我的简单概括存在误解的可能性,且《理想国》文本较长,精准找到对应段落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况且我懒orz)所以,暂且一提吧。
正义的定义
因为我无法完全把握文本的所有细节,所以下文便不多关注各个观点与结论之间的论证逻辑(虽然我觉得很多都没有逻辑),单纯把各个结论当作作者的希望来讨论。
理想国始于对正义定义的讨论,最初也是苏格拉底引入的正义讨论:
不过讲到“正义”嘛,究竟正义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有话实说,有债照还就算正义吗?这样做会不会有时是正义的,而有时却不是正义的呢?(331C)
特别是我翻来覆去看了许久的上面几段,确定在座的其他人没有提到“正义”这个词。然后便有一种苏格拉底(或者是写作的柏拉图)真心机的感觉,偷偷冒出一个希望讨论的话题,追着别人问正义是什么,然后又一一驳倒了在座其他人的正义观。当然是不是心机似乎课上还有澄清,但记不太清了。第一卷是经典的苏格拉底对话的套路:举特例驳倒别人,对自己的理论采取不完全归纳。多多少少有一点辩术的意味,因为不完全归纳是很容易举出特例的,只是在座的人都没在辩论中成功罢了。第一卷的结尾,苏格拉底回到了常规的状态——正义究竟是什么呢?依旧不知道。好在格老孔和阿德曼托斯拉住他继续谈,才把苏格拉底自己的正义观套了出来(当然这也不过是柏拉图的一种写作手法罢了)。
第二卷开始就是构建理想国,希望用城邦的正义来看出个人的正义。中间对话略去不谈,最后的结论是:对城邦而言,正义在于哲学家、护卫者、工匠三个阶层互不僭越,对个人而言,正义意味着理智、意气、欲望三个部分各司其职。这倒是一个高明的定义,算是颇有建树。但这个定义意味着阶层的明确划分,虽然由此各个阶层安于自己的工作,能够使得整个城邦最为完善,但究其个人而言,实际上是抹杀了底层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苏格拉底建城时,始终有一种置身城外,像创造者制作精巧的玩具一般的态度,哲学家应该被强迫成为统治者,护卫者不应有个人的财富与享受,只有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工匠需要安于被统治,在统治者的教导下完善自我,由此达到整体的和谐。这在受民主、自由等思想熏陶的我眼中,虽然合理,似乎并不那么合适。苏格拉底在后文探讨城邦衰落时提到民主的城邦尊重一切的可能性,也是一种堕落的表现,而如今我们更倾向于民主,这似乎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价值分别。这种分别使得理想国能否实现都成了次要的——即使能够实现,也只不过是苏格拉底眼中精巧的玩物罢了,并非我所认可的“理想国”。这倒是洗清了我阅读这本书的态度,从追求更优的理想城邦的图景转变为了解柏拉图脑内理想城邦的图景,因为二者已经不统一了。
能否达成统一?
于是此前粗浅理解中的男女平等、共产共妻、哲学家做王的图景不再令我羡慕,而是采取了更为冷静的分析态度。这三者的核心共产共妻,实质是为了消除私有,减少城邦崩塌的可能性,维持城邦的正常运转——没有私有,一切都是大家的,个人做的事也都是为大家,个人实现与社会实现达成了统一,理想的社会自然容易实现了。
不过这里当然要问,消除私有后,真的能达到个人实现与社会实现的统一吗?成功的例子实际上在每个人身上体现——一个人身体的各个部分达到了统一。柏拉图的个人正义是灵魂的三个部分朝着理智指明的方向共同前进,但身体本身则是一个良好的典范。我的四肢、我的内脏,不正在我大脑的智慧下有条不紊地各司其职做着工作吗?如果把一个人的身体看作一个社会,一个细胞看成一个人,身体的各个部分看作各个阶层,那么不得不说这身体真是达成了理想的统一境地啊。理想的国家中为了筛选优秀的人,甚至会偷偷杀死弱小的孩子与病患,也与废弃的细胞有同工之意。其实我在阅读《理想国》时,便时常觉得这个理想的城邦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稳步活动。
这个类比有两个方面可以思考:其一是城邦实现目标统一的条件。人的肉体实现目标统一,是源于单个细胞并没有足够的思维能力,也不会去追寻民主啊自由啊,但又能够承担相应的职责,于是大脑便达成了高效的统治。对应到城邦里,恐怕机器人才是满足条件的存在吧,用机器人取代工匠阶层以及护卫者阶层,然后由一个合适的管理者(哲学家?)统治,或许能够实现高效运转的城邦。但如果受管理的都是有自己想法的人,恐怕是很难做到,因为人最基本的自我保全与自我实现的想法是不能被忽视的,当然这依旧归结于自我实现如何与社会实现达成统一的问题了。
其二是如果细胞和人一样有了思考能力,或者现在就真有思考能力,那么情况会如何呢?如果是后者,细胞没有造反或者各自分崩离析的原因或许是作为一个个体也认为依附于一个整体是最优方案,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个体实现与整体实现的统一,这里的统一又分为目标的统一与行动的统一,细胞有思想时和整体的关系应该是行动上的统一,因为我预设了每个个体的目标都是自我保存与自我实现。
脑洞开得有点大,终于有点此前“书后闲想”瞎扯的画风了,再次声明以上胡扯和原文无关,纯粹是“真·闲想”。
零散的话
其实似乎觉得还应该继续谈一些其他的话题,毕竟《理想国》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哲学家追求善的过程,但想了想好像没特别想说的(即使说出来也难免是老师上课的重复),或者是我写了这么久(接近四个小时)已经有些疲惫了,瞄了一眼字数接近八千,算是刷新了最长闲想的记录了(此前好像是全球通史的五千)但这次是两本书,且积蓄了2016下半年的许多想法吧,多写一点也算告慰一下自己。
就像此前提及减少阅读方面的心思,结果一学期没写闲想一般,我觉得还是需要提升一下阅读与写闲想的频率的,当然也不再回到最初的高频了,因为输入端相比于此前已有了很大的扩充(课程方面),所以输出端相应地需要减少一点。但我也明白如果不常写点是什么,是会变得怠惰的,甚至在思想上考虑的东西也会变得薄弱,所以就让此文开启我2017年的“书后闲想”之路吧。
22:25 2017/1/2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