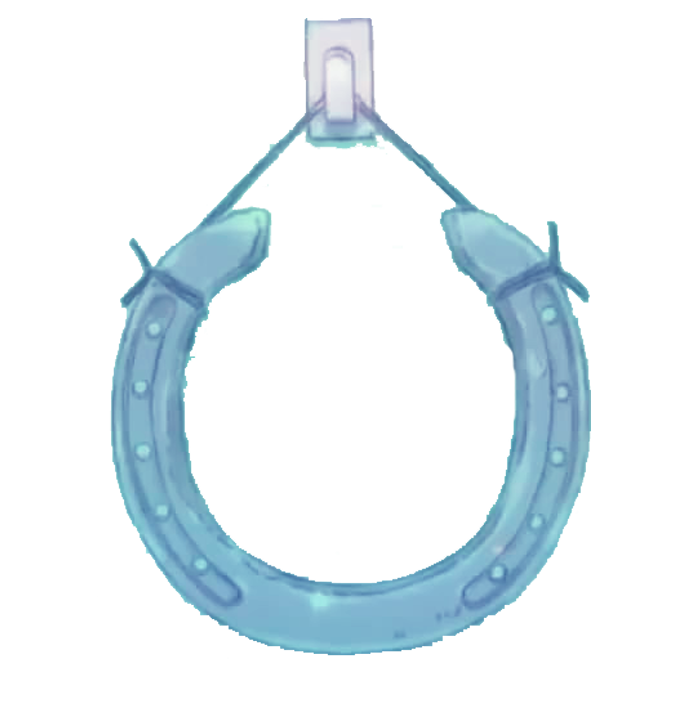可望而不可及的“齐物” ——《齐物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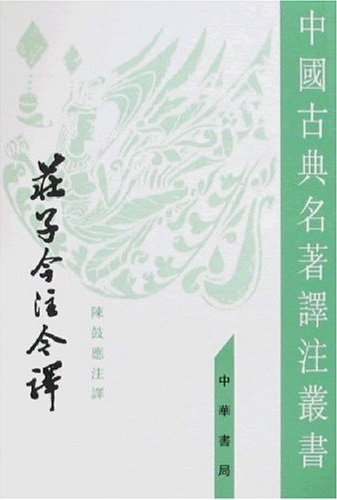
对《庄子》哲学,我是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了解的,那时印象最深的是“辩无胜”的态度。后来课本上也学过《逍遥游》和《渔夫》篇的节选,其意境与思想都是我倾向的那种类型——自由、洒脱、有反思精神。此前还曾就《逍遥游》中的“有待无待”问题写过一篇《打死结的无所待》,昨日翻了一下,发觉那时自己的观点还是非常现实主义的,认为无所待几乎无法做到,不如放弃而选择有坚定立场的“有待”。现在看来,对“有待无待”问题的看法也有所改观,在《逍遥游》的书后闲想中或许会有所涉及。
一直希望自己对《庄子》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课本上的残片,近来也去借了一些庄子相关的书籍。最先想着看看南怀瑾对《庄子》的口述解读,但后面发现不算特别靠谱,转而借了王博的《庄子哲学》与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后者是繁体竖版从右往左,而且非常厚(包括内篇外篇杂篇,注释十分详尽),一开始有点不太敢翻开,便决定先把《庄子哲学》大致扫了一遍,然后再两本书结合着读。后来上陈鼓应老师的课,他强调“要读原文”,正好我已看完了《庄子哲学》,便开始翻开那本八三年的旧书,开始一段一段地看、读。《逍遥游》因为课本上有一部分,读着相对较快,而《齐物论》,作为“论”,算是《庄子》内七篇中谈得比较详尽的一篇了。花了一些时间读完,终于再次遇到了那段“辩无胜”,最后也遇到了熟悉的“庄周梦蝶”的故事,感觉就像见到了老朋友吧。
对《庄子》与庄子思想的研究很多,所以在此一本正经地分析文本有种班门弄斧的感觉。况且“书后闲想”一贯来的风格就是谈我自己的看法,从文本而出,却不局限于文本。自认为光是读的这两遍,并没有办法把《齐物论》中的思想完全理解,只希望把我所得的东西在此做一个整理吧。毕竟有句话叫,“好读书,不求甚解”。
《齐物论》提出了一个概念,“成心”,就是个人的喜好与看法。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心,所以对事物的是非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便产生了争论,甚至冲突。而物是本无是非的,是人的偏好投射上去才形成了是非。庄子提出了一个“丧我”的解决办法,便是舍弃自己的成心,舍弃对“我”的执念。
个人认为我受庄子思想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以上一段其实有一种借庄子之言阐述自己的想法的感觉。因为我对《庄子》文本的解读,本就是在我的“成心”的基础上。我是承认个人不同的看法的,但我反对因此而产生的争论与冲突,因为这是无意义的,我们站在不同的立足点上,用不同的角度看一个事物,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但我们看到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如果承认自己所见并非绝对正确,又何以评判他人所见是否正确?“丧我”的最终阶段比较难达到,因为那时已经没有“我”了,而初级阶段的“舍弃自我的成见”则是可以具体达到的。这忽然给了我一种当时写《打死结的无所待》时的感受:庄子最为推崇的境界(如无所待)自知目前无法达到,退而求其次,选择适合自己的阶段(有所待而不为世物所累)。
不过说出对“个人的看法”本身的看法时,很容易就落入“呼吁他人遵守而自己呼吁的方法却恰好是在打自己脸”的情况。此时当然也有必要审视一下,我认为的“舍弃自我的成见”是对的,是否也只是因为我的“成心”让我认为的“是非”之一呢?无法否认。其实这种情况在下文中还会一次次遇到,比如需要以“辩论”的手法去阐述“辩无胜”,而这手法本身便是“辩”,是无法获得胜利的。对此,我的解决方案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齐物论》原文也有类似的话)我是觉得庄子的思想是偏向个人的,所要调整的大多是每个人各自的心态,而非对外物的作为。所以我希望的是用文字让他人影响自身的心态,而非直接影响他人的心态。毕竟文字至多只是表达了一种见解,接受不接受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不还有你的“成心”在挡着嘛。
去除自己的“绝对正确性”,接着得到的推论之一便是“己所欲,慎施于人”。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难做到,早先的文章也好多次谈起过这个想法。恐怕依旧要举那个常举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这是为你好”。多少人在这句话的庇护下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并以此自豪。个人觉得,当你说出这句话时,你不过是在说服自己罢了,让自己能够心安理得甚至十分用心地“帮助”他人踏上“正途”。我想对比较倾向的方式是“不可而止,毋自辱之”,这话是孔子说的,而庄子这里则是给它在理论的正确性上添上了一笔。总之,认识到人与人是不同的,各人也有各人不同的观点与追求,不必强扭,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到达的是一种“齐物”的心态,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万物各有不同,而在“道”上却有所相通。“莫若以明”,以豁达超然的眼光去看万物之分,才能抓住其内在的东西。虽然一旦搀上“道”就很容易走入一种玄而又玄的状态,“齐物”、“物化”之中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解读,但我即使是粗粗地体会,也还是能够有所得的。我不敢说我领悟了“齐物”,因为我无法说,我永远不知道我“成心”之下的“齐物”是否是庄子口中的“齐物”。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请允许我贴一段原文,毕竟最早我还没看《齐物论》时,光是看到这段话便激动不已:这不正是我追求的想法吗?两者辩论,没有人可以知晓哪一方真正正确。那退而求其次,一方成功说服另一方可以吗?这倒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但无奈实际上大多辩论的结尾,双方都无法被对方真正的说服,或者是“貌恭而不心服”,尤其是一种我最反对的,完全是为了辩论而辩论的辩论,这种结果往往是各自死撑自己的观点,尽力挑对方言语中的漏洞,舍本逐末地在打着语言仗。当然“辩无胜”并不代表“辩无意义”,对事物的理解的确是可以越辩越清晰,越辩越明彻的,只是需要辩者怀着“辩论是为了把东西弄清楚,而不是争个输赢”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我更倾向于把对话称之为“讨论”了。
《庄子》中时常出现的反思语段让我对它好感颇增,文本中总是会思考自己说的对不对,是否只是无意义的言语,而我也在这种反思中更为明白言语之间希望传达的精神(虽然依旧永远无法完全感受与理解)。如下便是一例: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这段是上文“辩无胜”前面一段,谈梦与醒难以区分,只有愚者才会自以为知晓。人们都在一场大梦中,而最有趣的一句是“予谓女梦,亦梦也”,连道破真相的人,也不过只是在做梦罢了。庄子用“吊诡”形容这样无奈的境地,并寄希望于有一人能冲破这困境,“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间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之感。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还有《齐物论》末尾这段让无数人浮想联翩的“梦蝶”说,也是道出了现实与虚幻界限地模糊。“齐物”的愿望是好的,而做到“齐物”的心态是很困难的,因为生而为人,便已身处在一个拥有特定视角的躯体之中,我们可以去想象,去感受,去接近“齐物”的状态,却又发现,“齐物”永远都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
这种人的局限性的悲哀在《庄子》中经常能够显现,做不到“无待”时的怅然也是之一。庄子无法看到“齐物”、“无待”实现之日,而我还是在心中抱有一丝科幻向的希望:在科学与技术的帮助下,人能否能摆脱自身的限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