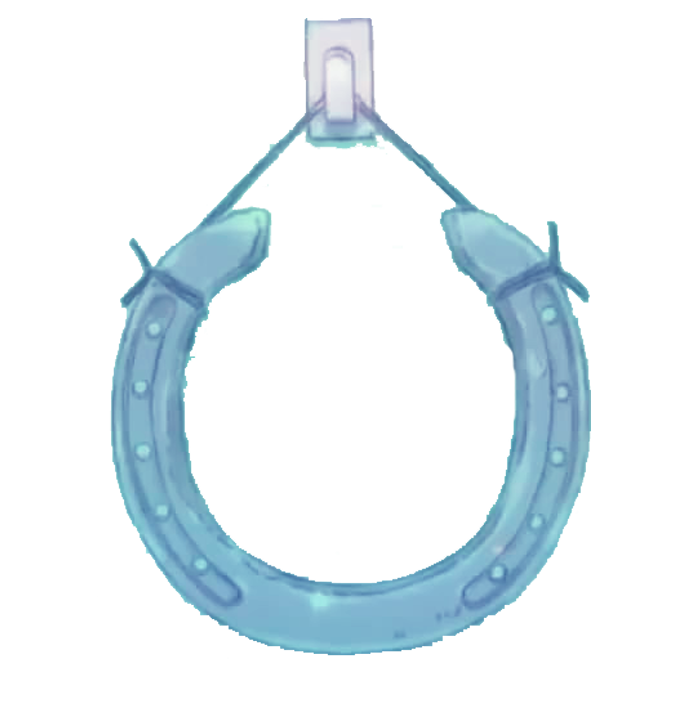可能性与控制论
前一篇像是《心理测量者》的“观影所思”,而这一篇则更像是《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的“书后闲想”。书后闲想的特点即是,除了少数语句和想法来自于作品原文,剩下大部分都是阅读过程中或相关或无关的想法。对于这本书,可能“控制论”这三个字着实于我最为重要,加上有关“可能性”的基本概念,剩下全是我自己的瞎推导,和原文思想可能无甚联系。
控制论的基本陈述是,被控制的对象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且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选择可能性。而我此前在可能性的魔术 中提出了一种对可能性的看法:“可能性的魔术在于对过往诉求的抑制,然后提出当事人并不想要的替代选择,以表观上唯一的可能性遮蔽所有潜在的无穷可能性,在A与B的选择题中遮蔽了CDEF的可能性。”但似乎总觉得还只是在陈述表征而没有涉及原理。
如今想到的点是,可能性的魔术在于遮蔽某些联想。极端一点,“可能性”这个词在我离开美国时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在北京的生活中却让我得以丰富其内涵,而回到美国时又让我忘记提起这些内涵。这里“忘记”的原因是描述某些精妙的点需要许多的前置环境、讨论基础,去掉这些之后直接描述事件本身甚至会进入一种失语症。
我在以做数学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某个点子冒出来时是处于某个讨论或者思考环境,当它诞生时会让人觉得一切都那么合理甚至可以直接着手去做。其中能直接着手做这一点涉及到与社会的交互,倒是可以随着对社会的熟悉而逐渐熟练,最差也能够将其记在备忘录中。而点子本身的消散是更令人沮丧的,这里的点子指的是新的生活方式、态度,是能让人不断改变发展的基础。
回到控制论的说法,人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论提升选择可能性的能力,但最初“存在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这件事却值得探讨。此处的可能性于我而言并不能是随机的,而应该是与此前已筛选固化的可能性相关联的。此处的关联于我而言大致可以被解释为与过往的见闻与思考相关,或者达成了我过往的愿望或偏好,这在数学中当然就是引用文献以及解决猜想,否则我并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关注新出现的事物,我也甚至可以搬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的说辞。
又陷入了长考……因为在尝试思考这种说法。其一是留学生社交泡泡就这么大,过往的抽样已能大致勾勒出模样,再拓展即留美工作人群以及美国华裔,其二是语言是一大壁垒,如果希望引入新的可能性则需要深耕英语沟通以及补充文化知识,这需要结合细致的生活实践。如果我笃定留在美国,这两者或许是我可以尝试开拓的,而我的过往经历和未来考量则让我选择了留在中国文化的舒适区。
那么在另一个场景,即回父母家时的思维封锁呢?过往我会遭受许多无形的默认束缚,比如在家就假定父母开车而非自己打车,进而丧失自己一个人外出探索的可能性。这种潜在的让步会导致可能性的急剧减少,生活也便落入了过往固定的模式,甚至思考也会陷入定式。过往的种种尝试是为这一环境注入一些从我的视角出发的规则与行事逻辑,再结合父母自身的习惯融入他们的生活,进而让我能看到改变的希望。
如果只有熟悉规则和适应规则,那么可能性空间只会越来越窄,最后坍缩至最优路径然后按部就班的进行。如果能看到改造规则创立规则的契机,那未知的可能性空间便会一下子扩大,让我的生活始终处在有选择、“自由”而又能导向我所期望的状态。我享受的掌控感是对这种不确定之物的把握与引导,或者说控制,使其在我的行为中演变成确定的成果并带来意义感。
一两年前讨论了许多有关虚无的话题,着眼在于发现、感受或者创造意义。如今狭义的意义感问题在我这里暂时隐退,因为我有许多可做之事与待做之事,我对它们无意义的指控大多出自于一时的恐惧,在勇敢前进之后这些事的意义感会自动浮现。此前消解时刻追求意义的疲惫的是沉浸感,如果处于享受其中的状态,我便自动选择放弃思考而随事物发展一同流动,这种状态在事后往往成为快乐的回忆,我也将其定义为幸福而努力追求并为之准备。
在对意义感与沉浸感都小有见解后,我自认为此后需要尝试锻炼的是掌控感。这里提到的掌控感大致为能够观察并开发所遇事物的可能性空间,然后通过现有的能力工具箱将其压缩到一个不论如何发展都令人接受的范围。在过往的经历中,失控的恐惧始终盘旋,意味着我需要时刻小心使得令人接受的范围非空。如今在解除历史包袱后,我在逐渐拓展可接受的范围,采取的基本方案便是为每个后果标定对应的“代价”,如果最差的代价能为我额外富足的东西所接受(钱、时间、精力、情绪),那便可以随意实行。这种状态让我的生活更为轻松,能节约许多思考。不过掌控感并不能作为目的,而只能作为手段,因为意义感和沉浸感往往是失控时的意外所致,处处有掌控感的生活反倒还需要额外的刺激。把掌控感恰好限制在失控的边缘倒是门技术活。此前提及的多个人格房间算是一种方式,至少使得风险相互隔离,且必要时刻可以唤醒房间总管。不过我在重新体验几回真诚的交流后还是觉得人格游戏有点无聊,还是先把博物馆关门谢客了。
22:25 2025年4月17日
感觉脑子里还是稀里糊涂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