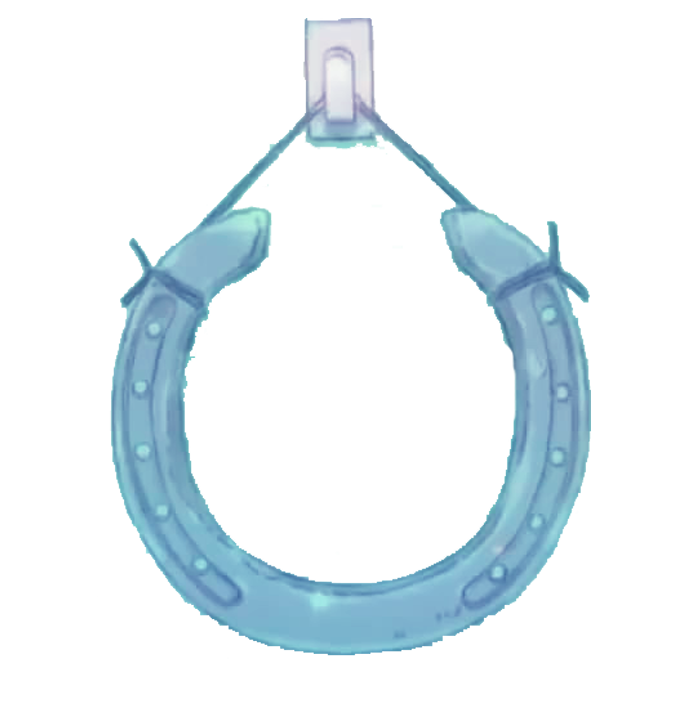信与利
此篇接续情与利 与情与义 ,在积极与消沉 的境遇下试图通过整体调整对待他人的处事态度,划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保留地。如同福柯指出,“精神病”这一概念是用以辨别“正常人”,我也只不过是用带有情绪与偏见的方式划出一条“我认可的”界限,以此来识别自我。再另一意义上说,与“常人”的斗争开展到了新的层级,我甚至不得不带着一部分被“常人”腐蚀的阴影继续前行。
与“常人”相对的是向死而生,当我终于处于随时可以“死”而无遗憾的境地时,死这一词的重要性似乎被消解了,向死而生也成了生死随意。反倒是此前对他人和自我有所亏欠时,向死而生反倒是值得被拿出来警醒自己不要迷失在常人的语境中的态度。而在浮士德时间,即喊出“你真美啊请等一等”时才会被收走灵魂,选择如何与梅菲斯特相处则是值得考量的点。与魔鬼相伴,可以尽可能的满足与享受各种欲望,但却不在这些实现中停滞不前。
“真情”自然是值得追寻的东西,甚至如今能被我抬到人生的终极意义。我喜于某位朋友在几经挣扎后,将真情从“再给我两分钟”演化成了一段更长的状态,使得原先“情与义”的探讨似乎能够告一段落。此后达成的共识是,维持这一状态需要进一步的各方面的努力,否则即是吃老本直到关系枯萎。若将真情作为最终方向,为之锻炼的各项能力,甚至细化到实操的各种细节,似乎都被赋予了意义。然而这实际上又让真情成为了赌注,甚至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另一位朋友指出在关系中仍值得保留独立性,忽然让我醒悟与如释重负。如今对爱的理解,也变得更为精细:
- 爱不仅要让对方自由选择而依然选择,还要让自己自由。不是必要之爱但仍然愿意走这条路。需要理清亲情、友情、自怜、自恋、感激、索求等关系,发觉期间被命名为爱的关系。不仅是为对方开心而开心,而是真诚地为对方以及自己的自由考虑却又相互接近。
自由如今被我看成爱与其他事物的中介,这篇文章 中的模型实际上仍旧生效,只是未来需要探索将应用于一人的模型延伸到两人。甚至这篇文章本想讨论的内容,信任(带来安全感)与利益(作为压舱石),实际上也在其中。只是那时的状态让我更轻松地关注“上层建筑”,而如今的境遇则又让我在“经济基础”上盘算,心理能级高下立判。
赘述这么多,其实是试图为过往的一段旅程稍作记录。此外,这篇文章 里提及的“纪念品”事件也在奇妙的机缘下落下帷幕,“直面被抛弃感”这一问题似乎在真情的论域下暂时没有新的具象化角色,甚至在波士顿后日谈中也能游刃有余地处理新的负面遭遇,让我完成了对波士顿的彻底祛魅。
然而在“利益”的论域下,抛弃似乎反倒是常态。如今我开发了“人性的弱点”这一黑箱用于在事件发生时封存他人,同时还有“遇人不淑”这一黑箱用以封存自我。这使得我能够不必在涉及利益的问题上纠结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所要关注的只是“利益”这一论域的大小。此前“情与利”的讨论中,我将“交情”也丢入了利益之中,如今这篇文章的主旨,怕是要把“信任”中的一部分也丢入“利益”。至于分离出哪一部分,使得真情的论域能不受侵蚀,这是需要精细关注的。
我过往并不希望为利益这一论域建立模型,因为我多少认为谈论利益是可鄙的,如今的解释是,还未对利益的侵蚀建立足够的防御,也还未对利益外的真情有足够的理解,不如先一杆子打死。如今尝试开展建模、讨论、实操这些行动,也尽可能将其限制在最低的范围。最理想的情形是,建立应对利益场景的基本模式,并尽可能地用手头多余的资源去换取不进入利益场景的自由。亦即,但凡我接受不去应酬的后果,我便可以不必去应酬。当然事实上整个美国之行的首尾便是应酬,而我如今的事业发展状态让我还不得不套上自由的枷锁去参与些许应酬,最多只能在应酬之余创造些美妙的回忆,让整个行程更“值得”。如果应酬是为了眼前的利益,那么对我而言是等价交换,而我追求的是应酬是为了未来不应酬,亦即未来长期的利益,这大概最多是二阶导为正,而在利益这个论域我也已经放弃三阶导为正的想法,因为风险与收益成正比,而利益这个论域本身于我而言只是压舱石,我闯荡的信念便不会十分强烈。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广义的收益,挣脱自由枷锁后的部分,即灵魂安放与梦想实现,实际上才是更值得搏一搏的,利益层面的东西,只是搏这些东西的筹码罢了。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中介与分界线。
利益可能往往指的是一个个体与整个世界的交互关系,而信任则至少涉及两个个体。我原先鄙夷朋友关系间“淡如水”的状态,并宣称与实际认为“这不是很容易吗”,因为在我的认知中不以利益共谋,而以互相认可为基础是朋友的基本定义。如果本身以利相投,那所需要关注的即是调和各方诉求,满足各方利益,并以项目为界,在此之外一拍两散,这之中对我而言根本不涉及“朋友”这个词。只是以往这一群体是“同学”,工作后变成“同事”,如今更广义的囊括了“合作者”。这里的这些身份只是关系的体现,同一个人可以既是帮忙签到的“同学”,也可以畅谈理想的“朋友”。而我做这一区分是为了分别考虑不同的情谊,如果要求朋友帮忙签到,有时倒说不出口了,因为自有别的“同学”胜任这一工作。
信任这一词在利益的论域里实际上“劣化”为担保,正如真情劣化为交情。做词汇的区分有助于我应对不同的场景,也能让我对他人的转述中更为精准地表达我的想法与态度。这让我想到更为“劣化”的词,即合约,甚至合同。此处的劣化指的只是我心中的重要性与所谓崇高程度吧。
担保也是需要有“信”的,此处可以用信誉,或者更准确的是声誉。前者是实质的信,后者是他人视角下的信。我可悲地观察到在利益的论域里人们是不考察信誉的,只考察声誉。此时说出“相信我”这句话毫无分量,只会被质问“拿出点实质的诚意来”。自我宣传在其间便可套利,或者说实际上是“套信”。我虽不深入了解美国文化,但我的暴论是美国强调培养自我宣传能力,正是因为朴素的表达不足以取信,亦即人与人之间基础的信任感不足。每个个体被抽象成提供利益的他者,如果无法展现足够的潜在利益便会被抛弃与忽视。或者当然不必执着于美国,我认为这是可以丢进“人性的弱点”这个黑箱中的东西,我在中国仍会遇见类似的说辞。只是在美国这是天经地义无需质疑的,在中国则需要背负一定的道德压力,使得套了一层“交情”的外壳。所谓两者取其优,于我而言,即是在中国适当将争取利益之心放在台面上,至少做到明码标价与童叟无欺,而两者取其劣,则是在美国仍旧遮遮掩掩做各种利益的包装,反倒让我开盲盒始终开出“利益”,而只有极少的境遇下才有“真情”的微光。而用利益换取灵魂安放、梦想实现的中介,即自由,的通道始终禁闭。那利益便只能“购买”劣质的享受,或者用于利益再生产的“声誉”。眼看着数字不断上升,可“享受”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因为并无定价权。如同股票抛出的瞬间才算作实利,于我而言,如果我收获许多永远看涨的卖不出去的股票,那对我而言就是“你图他的高息,他图你的本金”的金融骗局了。
此前我暂时的解法是东食西宿,如同人民币美元并不互通,实际上中美的利益换取通道也并不互通。对于一般等价物货币,可以通过跨国转账、银行结售汇的方式置换,但有每年伍万元的额度,利益结售汇的渠道便是自由,而银行对应的则是人的主体性。每个人的主体性当然有限,或至少在任意一个确定的时刻有限,但明确主体性的换汇额度与决策是否换汇,则是发挥主体性的关键之处。人们总追求财富自由,殊不知在这一模型的理解下,如果财富无限,换汇额度才是自由的体现,也是真正的“睡后收入”。在换汇额度之外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废纸或者虚幻的寄托罢了。于我而言,所得利益恰好卡在换汇额度之上是效率最高的解法,后者的提升当然十分困难,所幸我自认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后主体性的自由大大拓展,使得我确实又要转换为积攒利益的状态。
第三容器时曾纠结于“指向自己”与“指向他人”的差异与矛盾,如今的“换汇论”则让我更为轻松。所谓指向自己即为自己积攒利益,短暂屏蔽与他人的情感互动,指向他人则被细化为指向真情。此前指向自己也有为自己的梦想而孤身前进的含义,如今的梦想本身便包含与建立真情的人共同前进,并且维护主体性甚至在关系间甚至有益,这便让我心中的理论矛盾被弥合不少。我既可以允许自己短时间专注于利益而不分心,又可以放心大胆地享受沉浸感,只需在期间牢牢把握自己的主体性即可。理论的简化能够让我处事时无需加一大堆判定,使得控制论 的观点能得到更为轻松地实践吧。
我还不敢宣称在情感层面能够“直面被抛弃感”,但我至少可以开始尝试在利益论域内实践,积攒些许经验。我并不希望承认“人与人的关系最终只有利益”,即使这里的利益是广义的,但我至少可以宣称“许多人与人的关系里有很大部分是利益”,当我能够应对这里的“许多”、“大部分”之后,剩余的部分或许才会凸显出来,我再发展新的技术工具应对即可。如此先解决大部分、悬搁剩余部分,处于新的境地下再做考察的观点,确实是数学科研思维的一大实际应用。
目前利益论域中的被抛弃感来自于在美国这三年与人合作时的不受重视感,其一为步调被迫与合作者协调,却不得不忍受无穷无尽的“无法反驳”的理由,其二是形成科研品味 后单纯用言语甚至行动的表达无法受到合作者的认可。我曾苦于 初段少年始终无法走向二段,最后却选择了“逃离三边坡”。其中我(现在回想或者如今定义的)对自己二段的标准即是博士毕业后写出第一篇文章,这倒是确实实现了。而三段则是成为助理教授,这也在可见的未来能够实现。而后的若干段位直至九段,实际上都可以自己又当选手又当裁判的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单方面宣布胜利。所以合理的判断标准是设立一个个事业发展的梦想,并将这个梦想暂时以某一具体方式具象化,等到这一具象化的东西实现时,再回过头来检验梦想本身的放弃与实现 。在此基础上,二段少年最初设立的点实际上是学术独立,本想以寻求新的合作者的方式实现却几经受阻,甚至如今发觉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所以最后落脚点在与导师学术独立之上,那毕业后写出第一篇文章即是一个令我自己满意的判定标准。而如今我也可以谈三段最初设立的点是某位朋友的灵魂拷问“为什么要带学生”,这一问题当然是助理教授不得不面对与思考的问题,但我根据冲二段时经验意识到这背后的水也很深,所以我目前将其暂时定在作为coadivsor(共同导师)指导毕业第一名博士生,这件事倒是能在可见的未来实现,我也小试牛刀地做了一位本科生的毕业指导导师。与此同时我也不妨设立四段的目标为指导博士后成为独挡一面的科研工作者,以合作完成足以让其在学术界生存的工作为界。我在此不必赘述,晚些我也会直接为自己设立一个升段备忘录,并在未来自认为提升至三段时再写一篇科研随笔 。
上述说得这么详细,实际上指向的是,“面对被抛弃感”的一大办法便是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我在理性的层面上做了许多工作,诸如写了快十年的博文,而在感性与事业上仍刚开始。在感性的评价体系中,恐怕我还是个刚入初段的少年,才清理完个人历史中的悲情与愁绪,使得它们不会在夜深人静时侵扰我。而事业的体系中也将将二段冲三段。不过我倒是自信于我理性的考察,并在现今坚定不移地推崇哲学在生活的重要性。这确实是我对抗未知世界的最强力的工具了。
19:50 2025年5月1日
按容器论要迈向第五容器
而实际上转化为理性感性事业升段论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