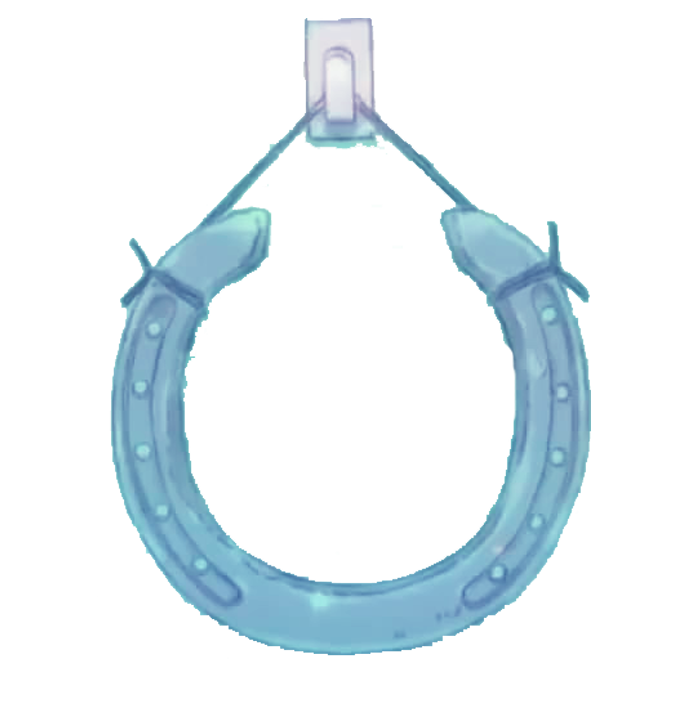协商与争取
自从在工作待遇上习得谈判心态后,我潜意识地将其迁移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处事是与他人谈判,规划是与(未来的)自己谈判。此处的谈判,指的是在明确自己所需的利益、能让渡的利益、拥有的筹码后,尽可能通过有来有回的沟通拉扯中让事情往自己希望而对方也接受甚至满意的方向发展。
我并不认为将谈判心态过度泛化是合适的,只是近来在逐渐磨砺使其能够加入工具箱。谈判心态的最大陷阱不在于最后的一城一池,而在于最初议题的选取,当没有选定范围以及设定初始共识时,沟通是无法开始的。然而这种选定本身就已经让无限大的可能性坍缩至一个有限维的空间,让一个可以勇于“争取”增量的问题变成了“协商”存量分配的问题。一种规避陷阱的方式是意识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拿不到”,即在谈判场外积攒谈判的筹码后再把对方拉回谈判桌,但这仍是一种谈判思维。
我曾自诩“ambitious(野心的)”,过往对斤斤计较的方式并不看得上,因为更专注于未来的前景。而如今需要也已经把一部分潜力变现,提升自己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协商心态在这一过程中能尽可能地提升变现效率,对变现总额要求固定时可以尽可能少地变现潜力(时间、精力、心力、健康等)。在试验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在协商能力这条路上继续前进,能触及他人的潜力,如果能引导他人潜力的变现,对我也会有正向的收益。投资“人”的想法出自这个角度,但具体的实现需要在互相信任、交流空间、合作方式上下更大的工夫,并非喊喊口号就能自然而然吸引到他人。
相较而言,投资自己的方式和成效都更可控,在自己的潜力仍有提升空间,还能够以力破巧的阶段,我会更倾向于专注自己的事业。我原以为人在某个阶段后会迎来强弩之末的感受,但那更多地是难以超越过去的自我(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如果在绝对意义上,仍可以有一波一波高峰的。在这一假定下,投资“他人”,提升协商能力,发生在上一波高峰后下降的低谷期比较合适,既可以用高峰时所获的外在成就提升交流时的自信和筹码,又可以让自己在低谷期有个承托。
而我注意到的事例中,往往低谷期转型后,在新的领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便也更无力返回来冲击更高峰了,甚至可以就此说服自己上限就在那儿,逐渐走向不争。于我自己而言,也容易陷入如此惰性的圈套中,但完成感和了无遗憾感仍会不时催促着自己再度挑战过去迈不过去地坎,直到达成一个自认为满意的当方面胜利。我还朴素地相信过去的愿望是更为诚实且对自己有益的,所以有能力后去实现,即使已经时过境迁,也能够让自己更为圆满以及收拾身心面对更强大的生活boss。
我需要面对的事实是只有我一个人有如此地执念与去实现的愿望,我需要逐渐明白、体会、宽容他人的不得已,不再像过去嘲笑《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的爆米花小贩,想周游世界却永远没有出发。现在会理解尊重祝福三连,然后买个爆米花继续走自己的路。不去实现的梦想如果已经满足了基本生活外的理想所需,那说明当事人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后,便不再会吸引到共同着手实现梦想的人。我需要警惕地也是不给人展现出空谈的模样,尽量言之有物以及展开实操。锻炼谈判心态后的优势是实操过程中有较大的拉扯空间,也就有了试错和学习的素材与样本。过往“被抛弃感”的恐惧也随之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大不了不玩这一局”、“下一把”的心态。
但真正涉及根本利益或者说自信源头的方面,比如科研进展、在意的人的评价与行动,依旧是无法淡化的。什么都不在乎对我而言也是反人性的。一种理想的方式是分散分险,或者“流行心理学”中的“增加人生支点”。我确实在某一方面这么在做,即将与某位亲近的人的交流限制在双方都舒适的范围,只在合适的时机尝试随机性突破,不行就退回原有舒适区。如此的缺点便是与某个具体的身边人接触就需要自动代入与其交流的语境,在多人接触中语境就会被急剧压缩。此外,能取得我信任的人便需要戳破这种为对方特地设立的语境,发掘我面对自己时会展现的那一面。博文里的我暂且被我自己定义为“真实”的,我也已经默认所接触的他人没有足够的心力与好奇去探究这一部分的我。度过一开始不接受这一点的过程后,如今我或许更为轻松地去塑造自己的另一个社会性人格。这一点对我而言实际上不太难,因为在我看来只是建个虚拟机,载入一些过往与他人接触的素材,便能较为轻松地训练出来一个模型,再与他人交互获得一波数据,就能在社交场合够用了。
那么人与人之间真正的链接呢?营造似乎存在的幻觉,便越让我对此感到淡漠。不论如何,让我至少维持自己与自己真正的链接吧,即那些外部展现的自我是内心自我的部分体现,而非单纯应付场合造出的假人。需要假人或者面具的场合必然存在,我不过是希望自己能尽力提升,以至于承担不参与这些场合的代价。
13:36 2025年10月7日
某种方面自信逐渐提升的
叶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