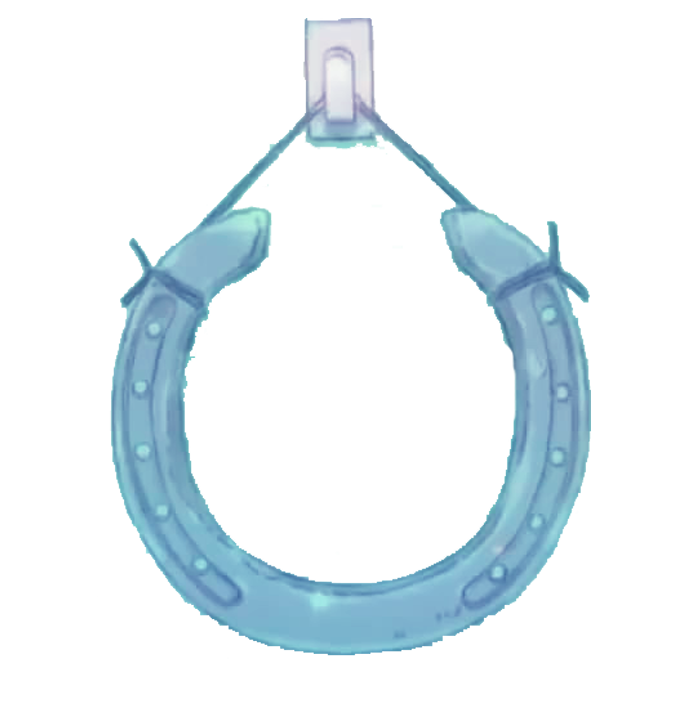虚无与空间
没想到虚无又一次地找上门来了,这次不再是身边朋友的访客,至少有一道隔离的屏障,而是光明正大地坐在了客厅的中央。在虚无释放它的气息时,我的工具箱中已有不少应对的方式,可无穷大的虚无需要一个无穷大的容器才能装下,现有的工具,或者梦想,最大的特点是它们是有限的,也就是随时可以被“虚无化”而“搁置”的。
自痛苦、紧张、压力被我识别为具体的生理反应后,虚无、孤独也从一种抽象的描述落地成了一种具体的状态。前几个月,孤独是稳定地访客,给我带来的状态我称之为“脑雾”,大脑在运转,但思考却没有指向,如果有一件具体的事,思考的资源便会注入其上,让我脑子“变得清醒”,并且迅速地得出许多判断。而如果无从下手,我大脑里清醒的空间便会变得越来越小,此时也难以休息,处于思维高度兴奋但空转的状态。参加社交活动或者上课,在那儿安静地听着便会缓解这种情况,因为思维可以用于分析社交中人的特性以及课程中的知识结构。当清醒空间大到一定程度并且积攒足够面对失败的勇气时,开展科研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此时科研已不再是过往投入时间换取快乐的转换机,而只是投入过剩思考能力后换取成果的时间精力保本器。这里提到勇气,是因为科研还是大概率需要面对失败尝试的后果,虽然成本也只是时间精力,但挫败感会出现。孤独的状态下本就脆弱,积攒足够的勇气实际上是接受挫败感的能力,这一方面工具箱里一些带有有限性的活动,如50%胜率的dota和80%能带来放松的剧与动画,便能做好承载了。所以与孤独共存,虽然艰难,但科研加工具箱加放松的模式多少还能自洽运转。甚至在第三容器时期已经有比较详尽的分析,如今的状态并没有比当时更糟,甚至还已经化解掉许多持续掉血的debuff,当然未实现的梦想和理想中的关系与可能性这些buff也消散了,所以也没有变得更好。
而虚无的感觉,说大点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说小点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孤独带来思考冗余,虚无则带来身体疲惫。身上的组织比较松散,没有一个坚实的念头让它们向一个地方使力。灵活的身体是肌肉张弛有度的,而全面的松散会导致一个杯子都拿不起来。好在目前的虚无只在极度疲惫、想做而没精力做的时候出现,但实际上我意识到是虚无本身导致睡眠不佳,进而身体疲惫。孤独导致精神紧张睡不着,虚无导致精神涣散睡不好。我曾从身体激素的角度试图解释,最终锁定在血清素和皮质醇。然而这些生化层面的解释只能大致告诉我原理,我也还没到失眠需要补充褪黑素的地步。目前我自认还是一个身心联动的问题,还没严重到抑郁症等病理性的层面,因为出门与人接触多少能缓解些,只是我的思想与决策导致我目前的状态,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而试图以精巧的方式平衡,或者等某个时刻掀桌不玩突跃进新的状态。
孤独与虚无的根源,于我而言是信任源的丧失。近来的许多人际关系转变,让我对新出现的人的平均信任度下降,从好处看是轻易地能够达成“尊重他人命运”、“先失望后希望”这种曾经他人口中“良性”的关系,也确实有更多的朋友能与我点到为止地轻松接触了。然而如今我连之前的人格房间都不需要开了,直接以本体性格与人接触都无所谓,因为人们对于进入我的房间并不太感兴趣,在外头欣赏一下大门就回去忙自己的事了。我希望有人拜访,还需要准备好各项“实利”,当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吸引人来多雨遮阳。
然而我并不想做大树,而仍对房间耿耿于怀。在无人敲门的情况下,我想做或者还能做的是将房间延伸到门外。大树与房间最大的差别是,树需要撑着与不断吸收养分,以实体与他人交互,而房间(room)只需要划定界限,以此中的空间与他人交互。我最终落脚在“空间(space)”这个词,一来取“第三空间”中的空间之意,而来取罗小黑中“灵质空间”之意。人格内部的部分我称为“房间”,因为我把人本身比作“房”,而间隔出的精神或人格区域是“间”,向外延伸时,实际上“房”便不那么重要,虽然仍需遮风避雨,但“空”的容纳性是更关键的。
这种拆词法有些学究,不如直接说说我心中具体的空间构想吧。此前与朋友的讨论始终着眼于“第三空间”里的“第三”,而我又始终关注“家”的构建,这在第三空间理论中是“第一空间”。近期因为一系列的遭遇,我在科研事业中突然有了建实验组的可能性,我也约了一间教室统一安排时间讨论,能够在试错中将我的科研组的设想落地,我也申请了域名,准备参考工科实验室主页的方式搭建组的主页而非个人的主页,隐去自己的重要性而将组内的成员向外展示。细节不多赘述,但这部分是“第二空间”的搭建。也就是说,在正式搭建第三空间之前,我准备先让第一和第二空间良好运转。如今第一空间已趋于完善,即使未来几个月还会有整体调整,我心里也有了基础的模板,而第二空间正在建设中,预计也能与我个人的科研事业相辅相成。而第三空间目前还只有“梦想合作社”这个名字的雏形以及一个域名。我还没有或者说没敢在里面填入更多具体的东西,因为它承载了更长远的时间线意义上的我的梦想,即陪在意的人实现对方的梦想。
第一空间落实,第三空间仍在务虚,近期第二空间的转变让我生活中的腰杆突然挺得更直了,虽然中间有期待过高导致的滑坡,以及救世主心态与相关的一些应激反应,但整体处于趋于平稳的状态,并且也能够消化我时有过剩的控制欲,或者说得正面一些是规划欲。第二空间对我的优点是整体可控,能够让我逐渐积累信任。做到这点的方式意外地简单,供给与资源足够时,主动剔除掉不可控的因素即可。过往人际关系的滑坡与对自我反应的认知,让我能在理性之前的感性层面便判断出不可控的部分,并且对事务层面的解除合作保持充足的理性,因为我不希望也大概率不会被“情与利”的混杂绑架。只要我不期待在第二空间追寻我生活的最终目的“真情”,我相信它能良好运转,并给我构建第三空间带来丰富的经验与心理支持。我曾经把数学当作哲学概念的试验场,如今又可以把数学组当作创业与管理的试验场。我也初尝“可控”或者说背后的“权力”带来的愉悦。数学圈内的共识是“影响力”,或者说口口相传,然后以此传播隐形的权力,即大佬看好的有更大的影响力,也就有更大的学术权力,而实验组内部则会将这种权力直接显现为各种各样的安排,如见面时间、科研方向。数学的一大优势是博士生对导师的学术帮助往往是无穷小,所以优秀的导师无法从博士生身上压榨与剥削出额外的学术价值,一种解法是佛系带学生,我也曾报以如此的态度,而如今我意识到学生成才这件事本身会给我带来成就感与回报,所以我只需要避免权力的滥用,便能达成师生共同促进的效果。这一点上,算是以身体力行回答了两年前一位朋友的灵魂拷问:为什么要带学生。
获得权力需要一系列的努力与操作,而使用权力和避免滥用权力则是更为精细的操作,限制的最直接方式是避免频繁的接触与过多繁杂的事务交流,以控制论的想法是控制环境而非运动的个体,以空间的想法是,将权力或者想法作用于空间的建设,而非空间里的每个个人。比如设立准入机制、空间里讨论的时间与方式,理论上一个项目的有效运转还需要空间外个人的时间投入,而这是非常不可控的,因为这将需要控制的空间从一个教室拓展到到当事人的整体世界。以有限的时间精力控制无限的可能性世界是令人疲惫与低效的,于是我选择让当事人自身成为课题的直接负责人和收益者,我的收益来自于空间本身,而直接断绝自己在当事人处的额外收益,即不和学生合作写文章。不过近来也尝试与博后的接触,其核心也是希望转化为对方的利益与诉求,如果并不一致,那便自然地选择下一位选手。以帮助对方实现自我来获取成就感与超额收益,我自认为是我的舒适区。只是过往筛选、资源、权力不足,导致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如今的试点是希望在这三者为正的情况下检验传导的比率,即自己能做100的情况下,带出的学生或者博后能做百分之多少。当我对这个比率有明确的心理预期和运作的理解时,我再提升自己科研水平的绝对数值,也能够为整个组一个明确的提升预期。
第二空间的理论分析实际反倒有些空对空,因为管理与运转是十分实际的事,也有直接的反馈可供我调整。大方向定下基调后便只是时间带来的经验以及对应的调参了。
第三空间理论的最初,指的是12个小时(睡觉加休息)的家庭时间,8小时的工作时间外的4小时时间的去处,曾经的样态是咖啡厅、小酒馆。其指向各有不同,有些只是消遣,有些是积攒社交货币(谈资),我曾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如今则精确到“我”与人之间的链接。也就是,我不再要求空间内的无我。这如今是我与最初提到第三空间的朋友最大的分歧,因为ta心中的第三空间是去中心化的客厅,人们可以随时来遇到有共识的人一同交谈。而我过往社团、编辑部、驻京办、研讨会的组织经历已让我深刻明白,我本身作为一个关键要素是必不可少的。用潮一些的话,我必须以身入局。或者以《非对称风险》中提到的,我在寻求一个能够“风险共担”的场合,那我本人必须要先承担主要风险,再去寻求共担的对象。此时的空间也不一定局限于具体的场所,而是人与人之间交互的活动与念想。不过对第一第二空间建设让我对空间环境本身的重要性也有所认知,因为共识往往不是写在黑板上让人阅读,而是通过氛围传达的。人在嗅到不合的氛围时自然会被拒之门外。
上面提到,我的梦想是陪在意的人实现对方的梦想。这一梦想当然可以有延伸与弱化版本,比如对不那么在意的人,我仍希望在少数几次的接触中帮助ta找到自己实现梦想的道路,只是我也不会消耗自己的时间精力“陪”。我在意的人,一个重要的特质是“负责”与“靠谱”,因为承担风险与参与实务在我看来是勇敢的表现,我虽不一定接受与勇敢的人共事,但我至少敬佩勇敢的人。“梦想合作社”这一名词初步的理解是,聚拢一些有梦想又有行动力和能力的人合作实现梦想,尤其是那些梦想破碎过而又重新粘起来的人。在我看来,有梦想而不去实现,只喊口号是可耻的,因为这意味着不承担风险只空想好处。这当然有父母的影响,在过往与父母的关系趋于平稳的这段经历中,我明确了空口畅想三十年与最终轻飘飘落地之间的落差,以及不做大梦但同时接受帮助抓住机遇用自己的奋斗改善生活的坚韧。自此我选择相信自己的眼光,为自己真正信与认可的品质投入资源。如今我不免有些自视甚高,看不上他人为梦想所做的细微努力,所以确实需要第二空间中更多关于他人的数据校正我自己对世界中他人努力程度的理解,再实践梦想合作社。因为单就目前我在市面上参加的社交活动中的讨论,财富自由、1000万赚睡后收入是普遍梦(瞎)想,主业不喜欢、想做副业或者三分钟热度也是常规的无头苍蝇之法,抱怨买醉也是简明有效的混日子与逃避之法。这当然是幸存者偏差导致的市面上流行的观点,因为真正在做事的人确实沉浸于自己的事业中。而我则介于之间,我既希望发展自己的事业(第二空间),又不希望仅限于自己的事业,因为我并不希望在事业中寄托我生活的终极意义。
不过不论如何,“三空间”这一叙事为我未来生活的方向定下了大致的基调,让我能够从过往“梦想的实现与放弃”后掉入的“自由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如今“能不能”、“想不想”、“要不要”的问题又可以浮现来考问自己,因为又到了检验一个梦想是否值得花大精力投入的时刻。“能不能”已经不再成为是非题,而变成了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的“我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一问题,答案目前还是“怎么都行吧”,因为事情本身便能用于对抗孤独与虚无。“想不想”倒仍旧有强烈的意愿,因为过往的努力让自由支配的(第一)空间终于转正,如今也想探索一番这些空间究竟能拓展到何种程度。对他人而言,这种空间从小虽然不多但总是正的,或者说小时候很大而如今受现实打压逐渐缩小,整体是令人沮丧的滑落,对我而言,倒是如今怎么操作都只有好与更好,因为过往根本没有回转和试错的空间,如今开始允许绕一些弯路也相信自己总能绕回来。“要不要”这件事倒是目前慎重考虑的,因为三空间表面上相辅相成,但建设它们的过程多少是有冲突的,因为都是先消耗精力(勇气、自信等)而寄托于长远的实际回报,当下的回报只是走在梦想的路上带来的看似虚幻而又最值得珍惜的充实感。经历过过往梦想的破碎与调整,当我着眼于虚幻时,充实感便会消散,虚无也会升起,而当我着眼于行动本身时,虚无又会退散。尤其目前我个人版本的第三空间“梦想合作社”承载了对抗虚无的无限性,反倒让我不那么主动地勇于向前,因为第一和第二空间是更具体更值得丰富,而做第三空间的纯梦是看似收益最大的。我要抉择的,是在缓慢推进第三空间的同时,在某个时间点将其确实落地。明年春天或许是个时间点,但我目前还并不希望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期限,因为我知道自己能感受到愿望与期限到来的那个时刻的心境。
11:50 2025年11月7日
建设三空间理论的
叶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