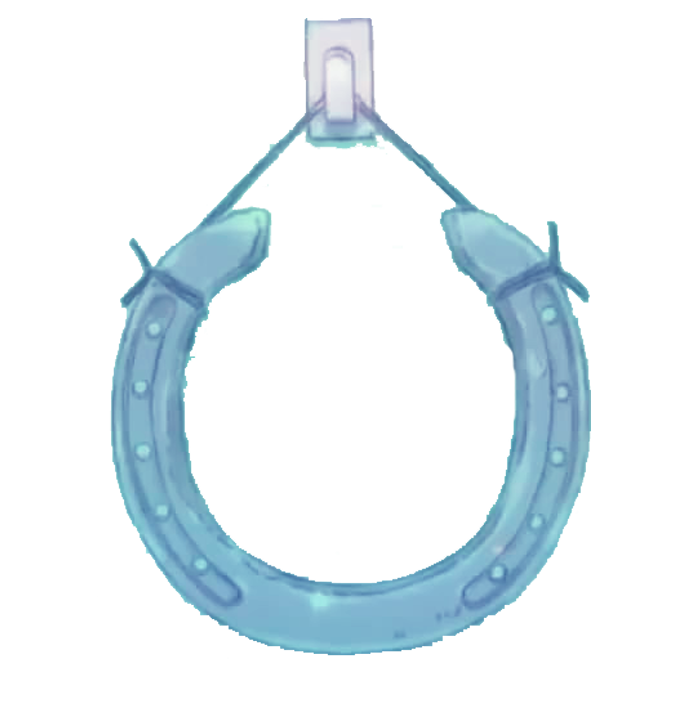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毛姆《月亮和六便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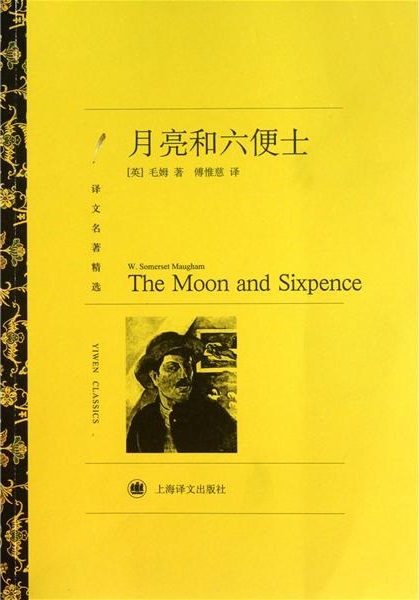
就阅读体验来说,《月亮和六便士》优于《刀锋》。
可能是阅读环境的关系吧,昨晚打理好杂事,在床上打开《月亮和六便士》,决定看到十一点就睡觉。结果在十一点时,我判断了一下剩余的部分,决定当夜看完它。
这次一开始我就看得比较认真,所以比较快地走入了剧情吧,阅读的过程中有种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快点把手头这一页翻过去的想法,但也明白手中的这一页也非常精彩,不容怠慢。此前看《刀锋》有种挑拣着、跳跃着看的感觉,而《月亮和六便士》没有给我这种感觉,看完之后,我觉得这本书的整体进入了我的记忆。
说了一些称赞之语,那该具体从何谈起呢?我是不习惯随着剧情,一一剖析给出见解这种形式的。所以讲到哪里算哪里吧。看这本书时,有很多段落让我感觉值得记录,所以这本书又是让我拍了许多照片的一本书,依旧是以前的形式,看图一张张来谈。
作品和《刀锋》一样是以第一人称写得,所以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有时也很自然地提到了一些和剧情关联一般的评论。如谈到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一本书中作家和读者付出的不对等,作家应该从写作中得到乐趣和回报等等。这种写法我在米兰昆德拉的一些作品中也又见到。夹叙夹议,而且议的东西深刻透彻能抓住我的心,我觉得如此便让这部作品的内容不局限于故事,而是蕴含了更多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理,这给这部作品增添了一抹亮色。
有时毛姆不仅仅要对文中的事情发表一下看法,还会对他写这部作品本身的状态进行吐槽。比如吐槽自己的人物写得不够有血肉啊(虽然后文成功地塑造了这些人物的性格)、吐槽自己了解到的资料不够多不敢瞎做改编啊猜测啊、吐槽本来想让故事在这里结束却发现顺叙更顺手啊之类的。让我有一种作家坐在面前跟你聊天,边讲故事边自嘲的感觉。随性自然,倒是拉进了我和作家之间的距离。另外这会让我有种毛姆就是文中的“我”的错觉,以为这些是他的真实经历(毕竟书中的“我”就叫毛姆),我觉得这就入了他的套了,这些故事虽然看上去向旁观者,看上去说了那么多写作时的困难啊状态啊,可归根结底连这些困难和状态,都是作家笔下虚构的呢。包括《刀锋》其实也是类似,大题都是以“我”的视角来写,混淆现实和虚构,如此之法,更加真实吧。不过还是那个老想法,能打动人、改变人的故事,为何要在意真假呢?它的效果就是它的全部了。
由于刚看了《刀锋》,在看《月亮和六便士》的时候就有一种对照感。前者是毛姆的晚期作品,而后者早一些,可以看出来更加热情奔放、理想主义一些吧,看起来也更加动人心弦。(《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而我却还是最喜欢他的这部呢,因为老来写出来有总括性吧,但托翁却没有失掉那种年轻的活力。)
主人公(很抱歉我记不起名字)走入故事的开始和《刀锋》很像:告别原来的生活,重新开始,为自己心中的想法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看着这两本书,我觉得它们不断地在问我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毛姆的这两部作品其实是给出了两个他认可的实例,一个为思想,一个为艺术。都是理想主义的,都是超脱于周围人的平庸的。不过,书中的“我”一直是一个看上去不太支持主人公行为的人,他和主人公有几次对话,每次双方都直入主题,针针见血。“我”提出一些现实中周围人的看法,包括一个人应担负起的社会责任。这些说法并不是世俗化的说教,而是一个有识之士的确是需要考虑到的,很可能也是某一部分的我会去选择的。而主人公却对这全部十分不屑,家庭、爱情、事业,在理想面前都不过是尘埃罢了。主人公的粗野给人(就是书中的“我”)一种不通情理的感觉,而我想毛姆就是希望用这么一个有点不讲道理的“死脑经”来体现那种对理想的狂热。看过《赤壁赋》后,每当看到作品中相互交锋的两种声音,我总会认为这是作者内心的两种状态的交流,他的理想和他的责任。所以毛姆让这两个人物的关注点几乎没有交集,由此可以展现心中两种想法的冲突。
这是一种夸张,我想现实中的人基本还是两种态度都有点的。对我自己来说,我只能做到摒弃那种世俗化的见解,却没有办法在两种我都很认可的意见中做出抉择。书中的“我”和主人公的几次对话中,我时常觉得,“我”说的很对,而主人公却无情地表示蔑视,由此我产生了和“我”类似的想法,而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主人公的选择也无可非议。怀有这种心情,我成功地融入了文本,期待着事情进一步的发展。小说吸引人的关键在于你需要体会到书中人同样的感受吧,那之后,书中的人物似乎成了你的一个投影,他的命运和你的心意息息相关,在不知不觉中,你便跟着他走过了一页又一页。
忽然想起来,这种状态还是许久没有了呢。看的书的种类多起来了,看得小说变少了,长一点的小说便更少(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我都是以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看的),之前和人散步时提到上一次遇见让我读的兴致盎然的小说已经是挺久之前了。我能马上想起来的是《岛上书店》,再上次?虽然总数不少但是似乎都已经过了很久了。
说远了,还是回到《月亮和六便士》。继续说说书中的人物,两本书看下来,觉得毛姆笔下的人物基本都有通情达理的一面,有我认可的一些品质,例子就不举了。用术语来说,基本都是“圆形人物”吧,而且都是透着人性中的善的。没有反派boss,困厄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现实,来自于各种人们不经意间的细节。如此的人物体系我还是十分欣赏的,这让每个人物(至少是主要人物)都有了可解读的地方,也让我能够有可能喜欢上他们。虽然有一些人物有所转变,先通情达理后面也做出一些比较反面的事或者有一些比较反面的心态(《刀锋》的女主和《月亮》中主人公的妻子),但我觉得还是对她们讨厌不起来,我想这也是毛姆文学能力的一种体现吧。我还是一个写作时希望自己能够喜欢上人物的人(比起只把人物当做工具来表现情节),所以我想毛姆在这方面可能也会对我产生一定的影响吧。
关于理想主义,其实有一个点值得讨论。书中的主人公四十岁抛妻弃子,开始画画,因为心中有种强烈的意愿,而最后他的确在绘画上有不小的成就,于是可以传为佳话。那若是由此默默无闻,就这么融入历史的浪潮呢,如此的决绝是否就成了笑柄呢?书中的“我”确实提到了这一点,而主人公的回答是不在乎。而最终主人公的结局是成功的,所以他的这句不在乎可以说的比较有力。如果失败了呢?一个可以过安稳生活的人,忽然抛弃全部,走上追寻理想的道路,却发现自己的理想完全是一个死路,自己完全不可能实现理想,这种状态下,该是怎样一种感受?可以说,只要追寻了就是意义的全部了,人生在世看经历而非结局,不必关心旁人的言语,这些话可能早些年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并坚持,而现在似乎多了一分犹豫?因为我想我在说这种话的时候,其实还是潜意识中坚信自己是能够成功的。
正式地提一个问题:注定无法实现的理想值得去为之追寻吗?关键词是注定,没有任何希望。
忽然觉得这个问题和上次的《入殓师》随想中的问题很像:当一个人注定无法跟你再进行任何信息交流时,那个人可以被认为对你来说是死亡了吗?
虽然这都只是一个思想实验,现实生活中不会有如此的情形,但我想既然是思想实验,就应该做的绝对一些,那样才能思考的更加透彻,不然总是会有别的情绪混进去。
各类作品中不乏有绝对绝望最后还能够闪现希望的例子,毕竟就这么Bad End也太负能量了,作品本身就应该唤醒人们前进的动力啊。
对于以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按照理性判断,应该是不值得追寻的,但因为现实中总是混杂着希望,所以如果要从乐观的方面讲的话,这个问题似乎本身便不成立——如果已经失败,那就后悔过去没有意义,如果已经成功,那就不是注定无法实现的理想。
怎么说呢,这种自问自答似乎比较没意思,但我又觉得去想想还是有必要的吧。可能会有更好的解答,现在我只能用取消问题来回答问题了。
写得有点长了,可能在浓缩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这方面还有所欠缺吧。回过头来似乎真正表达的理性的东西也不多,都是一种感性认识吧。
最后还是把书中的一些话当做推荐词吧,有闲心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本《月亮和六便士》,写得很……想个形容词,贴心吧。
“作者应该从写作的乐趣中,从郁积在他心头的思想的发泄中取得写书的酬报,对于其他一切都不应该介意,作品的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誉或是诋毁,他都应该淡然处之。”
“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到美德。”
“那些告诉我他们毫不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的人,我是绝不相信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无知的虚张声势。他们的意思是:他们相信别人根本不会发现自己的微疵小瑕,因此更不怕别人对这些小过失加以谴责了。”
“人们说服自己,相信某种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甘心为它效劳,结果沦为这个主子的奴隶。”
“如果他为了一个女人离开你,你是可以宽恕他的;如果她为了一个理想离开你,你就不能了。你认为你是前者的对手,可是同后者较量起来,就无能为力了。”
“叫人做出高尚行动的有时候反而是幸福得意,灾难不幸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人们变得心胸狭小,报复性更强。”
“人们动不动就谈美,实际上对这个词并不理解;这个词已经使用得太滥了,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因为成千上万的琐屑事物都分享了‘美’的称号,这个词已经被剥夺掉它的崇高的含义了。当人们面对面地遇到真正的美时,反而认不出它来了。”
“作家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