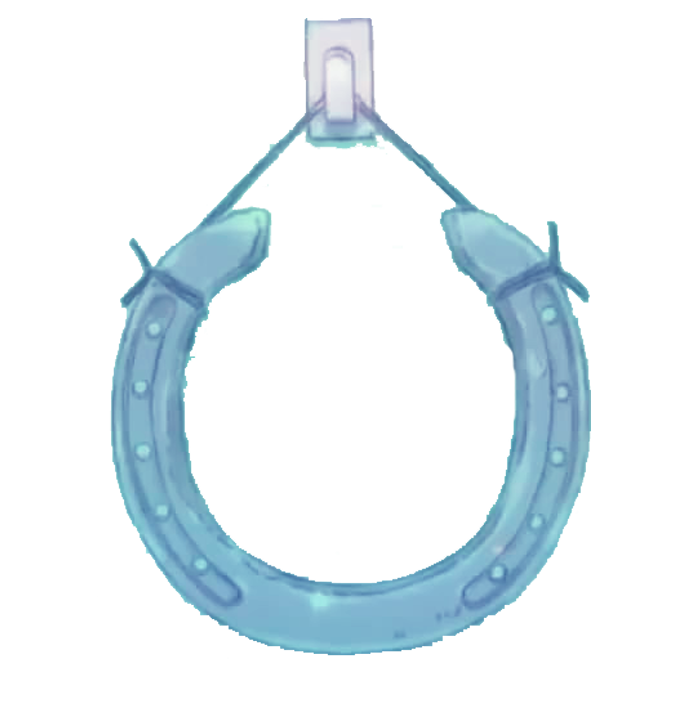主线与支线
所谓务虚、复活,在如今的语境下指的是能不加掩饰的质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亦即“当下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而当这个问题有了“爱,然后数学”的回答后,下个质问便是“现在所做是否指向它们”或者“如何做才能指向它们”。我在一遍遍地拷打中完成自我认同,大刀阔斧地裁剪生活的支线而专心为主线服务。
世界(外界、生活、命运、或者什么别的词)最喜欢开的恶心玩笑是在人犹疑与虚弱时兜售额外的愿望,并在人放弃当下看来遥不可及的目标时轻描淡写地实现以了结,由此便只剩下对强加的愿望的欲求。这算是《在云端》给我带来的教训,也是《周处除三害》里邪教的处事风格。而生活中的“常人”事实上也扮演这样的角色甚至身体力行的实践并乐在其中。
近来受孤独侵扰,试图以各种主动地方式与人或世界产生联系,大数据的推送也变得越来越情感大师,仿佛学会几个技巧便能制霸社交圈。对此般话术过往信奉理性的我必然嗤之以鼻甚至感到不解为什么画个圈便能圈住这么多人,如今时常暴露自己的脆弱时才意识到这确实是这种境遇下消解不安的代餐。脑内不由地又盘旋起《存在与时间》中的“沉沦的必然性”。去年在事业层面几乎再度掉入沉沦,没想今年在情感层面的沉沦机制又悄然启动,只得说不愧是生活的巨大boss。
实际上对抗沉沦亦是我生活的主线,并且我对此极为敏感,凡是涉及“闲言”、“好奇”、“两可”的日常语境与熟人,都会令我多少产生一些恶心并希望回避。我的原谅也仅限于我的朋友在我不在场时。而对日常的闲聊,我确实仍未掌握打破八卦语境的能力,而不时给出社交礼仪式的发问。但这或许是锻炼能力的支线,必要时刻我仍可以选择沉默。
产生主线与支线之分的原初假设是沉沦是个会抓住一切犹疑虚弱时刻无孔不入的庞然大物,我穷其一生也无法彻底战胜而只能适当领先,而我为了不被锤倒只能不断地将生活锚定主线上而在支线上点到为止。前者意味着,只有爱与数学带来的美妙时刻能让我驻足停留并渴望延长,因为它们已是最终目的。而后者意味着我对新的与旧的兴趣,不论是常规的运动社交,还是独树一帜的环游与了解世界与文化,甚至是过往追寻的执念构建理想的旅居状态,都会被视为实现前者的手段。许多支线可以不断精进而永无止境,而我会选择在大致摸清情况后打包封存以待未来所需时再打开与延续。
新的兴趣确实会涌现,如前几个月关注的人类学,但如今这种“务实的务虚”已无法吸引我投入许多时间了,因为它像是社团,无关功利而由爱好驱使,有时也会画个过大的饼招徕新社员,而我可能试吃过就跑路了,因为将它作为手段时是难以体会其精髓的,我需要在某一时段意识到它能与主线合流时,才有更大的动力前进。
不得不提,过往对主线的勾画,受到了父母或多或少的影响,使得在支线上倾注心力成了自主的出口,而后发觉培养的支线与主线的合流甚至取代原本的主线时,有种欣慰与释然感。而如今独自描绘主线时,似乎还不足以有额外的心力处理支线。这点让我想到培养自己科研品味时秉持的观点,即只做自己关心的问题,因为每个问题实际上都一样难。经历如此观念改变后的数学科研才能称之为我的最终目的之一,近来所试图做的观念改变便是将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另一终极目的“爱”之上。寻求各式各样的爱都非常困难,那便朝着自己希望的爱前进吧。毕竟过往得到的深刻教训是,难以实现的事物,舍弃了重要的东西可能仍旧难以实现。数学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舍弃对爱的追求也做不出来,当然追求不到的爱就是追求不到,压抑对数学的念想也追求不到。一个成熟的数学家或许已经习惯长久毫无进展的沮丧时刻,而仍然着手工作等待未来某刻的灵光一闪,这份无奈的耐心可能也是在一次次失落中磨砺出来的。我的情境毕竟好一些,过往有不少幸福时刻,眼下的投入也以不断更新迭代自我的方式产生无穷小量,生活的重锤也还没切实落到我的头上,那便挣扎着等待吧。
16:20 2024年3月19日
暂时独自一人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