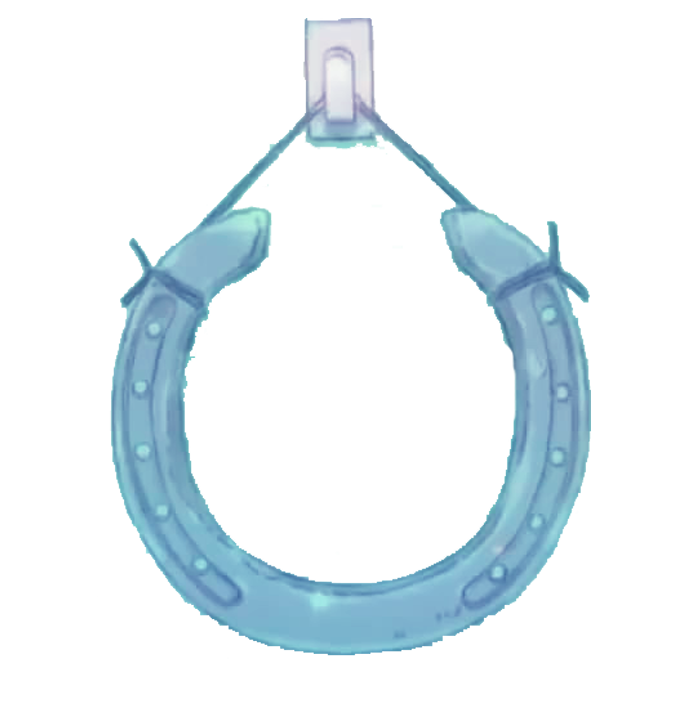生存与生活-续
大学以来,我的活动基地以北京-波士顿-剑桥-北京-剑桥-波士顿的顺序变化(严格来说我并不在波士顿而是波士顿隔壁的那个剑桥),第一次到达这三个地方时,些许对应着三个容器 的开端,前两个容器由于结束时的变故以及长期积压的不顺心,在我到达新环境后被我主动抛之脑后,甚至刻意减少回望,而第二次到达这三个地方时,对应着某种释然和重新面对与理解以往的问题。
第一容器的问题在我看来已经与当下的我彻底和解(对于过去的我,很无奈时间已经逝去而我也无法改变过去的遗憾)。再度来到北京时,最初一段时间也有过往痛苦再临的担忧,甚至叠加上一层第二容器带来的阴霾,但随着时间的前进与各类活动的展开(驾车出行、旅居、每周驻京办、时常开黑吃火锅等),到最后我受好友的感染阅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并重启阅读与闲想写作,算是让第一容器的闪光之处成功整合,也让我终于明白并切身体验了我想要的生活(至少是一种样例)。
第三容器的出发点是彻底指向生存的,由于追求长期的事业生存而让自己短期内仅保持基本的生存线。我本希望安于此,但后面发现,生活里有些东西最多被短期减掉,最初发觉是通识知识的摄入,后面发现娱乐也不可少,再后面发现社交也是必要的。缺少这些事物的生活,短期内可以运作,我也大致归纳出这个期限是两个月左右,运作过程中,我消耗着过去积攒的精神力或者幸福感,全身心投入到我的事业发展中。这种必不可少最初体现在阅读《存在与时间》后得知“沉沦的必然性”带来的幻灭感,而我在第三容器中实际上就在与这种幻灭感做着斗争,虽然我其实不自觉。当我借由第一容器的经验与体会,把理想的生活这一问题得到阶段性解决时,实际上第三容器的核心问题在不知不觉中也被消解了,这也是上一篇《生存与生活》极其之短与贫乏的原因,因为我完全知道这一回再度来到剑桥时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日常状态。
计算了一下,这回在剑桥只待了45天。最初四周在思考之前提出的科研上的一个点,然后是毕业答辩,再是集中性的哲学阅读,以及贯穿始终的研究如何尽早跑路到达下一个阶段。对于娱乐,我有意识的加入了看剧和打游戏并不以为耻,看优秀公开课,与朋友线上沟通,甚至晒太阳都被纳入了改善状态的有意识的举动之一。这有点像以往积攒的工具箱里已有许多有用的工具,让我能在合适的时机掏出对应的工具立马解决。但最后数日依旧有些精神紧张以至于头疼与不适了,不过倒也是在意料之中,因为以往的工具箱能应对在剑桥日常的自闭生活,将我的精神状态维持在一个还可以的水平上(即使没有任何当地社交与娱乐),而最后数日则是我通过各种高强度的努力让我离开的时间提前了20天(一开始的一次决定提前了10天,此后又一次提前了10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二十天我待在波士顿(plan B)或者踏上回国之路(plan A),都是赚到的,所以不论我在暑假选择plan A还是B,首要事件都是让我尽早离开。这一努力的结果我还是十分满意的,因为这一周在波士顿便发生了许多不可替代的活动(两个会议、若干这周才能约到饭的人)。当时我希望通过爆发自己的能力,研究出plan A能够顺利施行的办法,并且当时时常觉得如果能在更合适的时机做一些事,说不定plan A就能成功。最终plan A由于我爆发点还是太晚,施行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而我在波士顿这一周的经历也让plan B更加鲜活与吸引人,于是我便终于彻底放弃了plan A,而投向另一个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道路。
有目标时前进是容易的,而接受目标并决定才是困难的。于我而言,这种事情在三年前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两个不太合适的方案中被迫选择一个(当然也可以甩手走第三条路径,但事后诸葛亮来看第三条路径会由于疫情而大翻车),我为此几经摇摆,将心中两个方案的优势与劣势逐一列出并加权比较,但同时又知道这种列举只是理性对意志的一种安慰,意志往往会因为一些说不清的小事而做出最终的决定,而犹疑与改变想法则出现在另一些小事发生时。清晰地记得,因为获奖获得了免费来回的机票,我能够短暂美国的环境回到家人的身边,与家人一起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此后的经历不过是进一步地验证与确信罢了。由于两个方案都不是最优,如今反过来看只能说是,我靠着自己的能力、他人的帮助、时代的大环境,让这个差中选优的方案诱导了当下两个优中选优的方案。当时选择任何一个方案,心中依旧都需要选择某些痛苦,而如今两个方案的选择,实际只是正面意义上的生存与生活的选择,plan A可以让我再度体验理想的生活,为我的博士甚至学生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plan B则让我提早为事业而再度踏上奋斗之路,但波士顿是一个一分耕耘n分收获的地方,仿佛一支优质股票,我可以不惜加杠杆也需要大量持有(四年前或许是加了个大杠杆,如今不过是放弃难以实现的plan A罢了)。
这个意义上,这次选择更接近于三年前的暑假,我在获得博士第一个课题后,在踏足多个城市与提早开始课题之间纠结。那时也是生存与生活之间的选择,只不过那时我对选择后的所得一无所知,更有赌的成分。而如今来看,选择生活对长期的我来说是正确的,因为大学毕业、科研开始前的时光确实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当时的出行选择也影响到了近两年出行的目标与心态,在我看来是解决“理想的生活”的必要一步。其实这也是我此次极度倾向于plan A的原因,即使刻意在plan B上疯狂加码(指计划让我心动的活动),心中知道如果plan A能施行也会选择plan A。和三年前相同,学生时代最后的假期是不复再来的。林中岔开两条路,我努力地清扫一条路希望涉足,而时代的洪流却让我选择了另一条路,这种被迫的选择在一周前让我精神紧张而头疼,如今却更为平静的接受,而不知未来事后诸葛亮会如何看待呢?
在遭遇波士顿丰富的活动后,plan AB之间的抉择实际上在我心中已几乎成为定局,但最终的决定还是在与最好的朋友通话后落定的。回想当时与第一容器和解时,也是我心中几乎有一个明朗的画面,而在与最好的朋友对谈后让它在我心中彻底被打包和长期实现。能有一个人在我人生的重要时刻,在一旁倾听我内心的犹疑和最终的选择,让我感到感激与幸福。人生的道路或许被一个个重要的选择所决定,那些站在岔路口为我举着路标甚至引路的人,都是我人生中闪亮的星。
在plan B下,依旧有一个细分选项需要我去抉择,我在决定plan AB之后才开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这便是是否要去欧洲开会/旅游和是否要在美国旅游。这在我看来是两种含义的生存(疫情与事业)与生活夹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在plan B的大优环境下再选优,这种相对值反而在我心目中不太明晰了。对欧洲之行,我也数次摇摆,目前暂时摆到了放弃这一侧,或许基础的原因是疫情在我心目中依旧占比较重,而能说服自己的核心原因是我希望让日常与心境尽早稳定下来(我为了与上述“生活”区分,选择用“日常”代替广义的生活)。因为我也深知,烦乱的思绪与不确定的行程会让科研状态十分糟糕,反而会让我丧失plan B自带的优势。而在美国旅游,则是一个疫情、视野、生活夹杂比例不一样的另一个活动,我还没有完全决定,只是暂时将其他事的安排调到更高的优先级吧。
回到plan B的基本状态,即在波士顿的日常。按照第二容器的经验,波士顿可以让我在科研及科研相关的社交与活动中高歌猛进,而这带来的忙碌、激动与快乐往往会短期掩盖内心状态的演变,以至于在某个临界点曾让我陷入内心无所适从而不希望在科研上再投入的心境。由此带来的对内心寄托的强烈渴望在没有合适引导的情况下或许会造成更大的痛苦。如今来波士顿第一周的忙碌退潮后,我不得不在这一时刻预先提醒自己这种潜在的状态,因为我在剑桥时更多的纠结于planAB而对新阶段没有明确的理解,这和回剑桥前已经用一段时间想明白那里的生活状态很不一样。我以往写过三篇对过去的解答,可以看作对第二容器后期种种心态与疑问的回答,而那是建立在把波士顿的生活当作过去的前提下的。而如今波士顿的生活便是我的当下,所以我虽然看似解决了第二容器的问题,但或许是让当下的我能够接受过去,而如果对当下的生活没有足够的意识,那么促成以往第二容器问题的环境或许会再次催生与第二容器相似的问题。
当然如今的我也不像当时那般野蛮探索且带着些许第一容器的痛苦的隔绝。我从《社交的拓展》中其实便已有起头思考配置新环境的事,如今也只是在激动与纷乱的活动中提醒自己一下罢了。顺便一提,原本《存在与时间》的重读(与读完第二部分)是安排在剑桥生活中的,当时的心境确实会让我对孤独的心境有更深的理解,可惜当时各种事堆在一起,而我又想着逃离那种孤独的心境,也没有时间去探索孤独状态好不容易暴露出来的新的内核。如今到了新的环境,心态也大为转变,我至少不必为心中孤独带来的痛苦而每晚辗转反侧一个多小时了。但我想《存在与时间》的阅读不能就此搁置,我还是要在这个暑假抽出一段时间将其读完,并尝试回顾一下以往的孤独心境的,不然似乎无法为过往的哲学理解花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并不有利于未来的前进。当然我原本还安排了法国现象学和其他一些当代哲学家的阅读,但我觉得这个阅读计划倒不是很急了,留在合适的时间展开可以给我进一步心灵力量的提升。
写到这里便先戛然而止吧,装备了以往经验的我再度面对波士顿,希望能够游刃有余吧。
10:43 2022/6/19
算是还在第三容器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