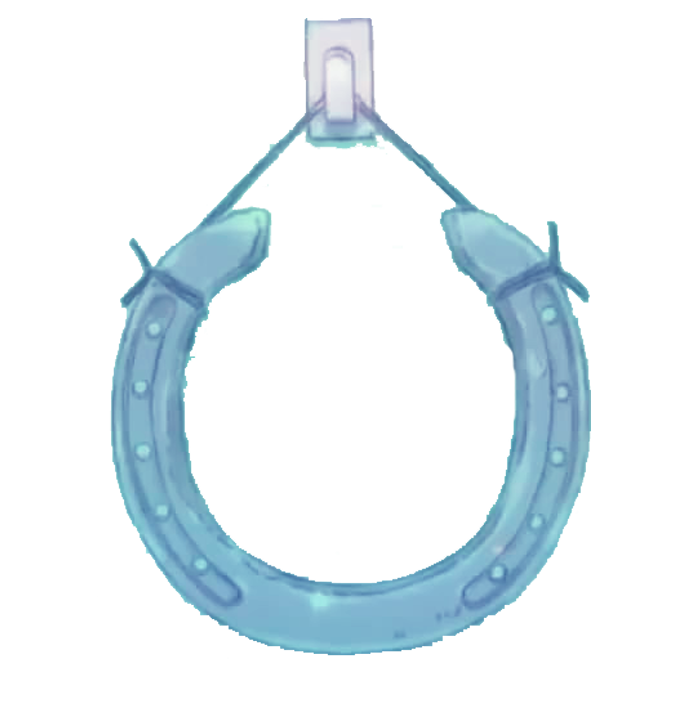世界与自我
这篇又是年更的生日文,前篇指路 未来务虚导论序言
按照惯例,先回顾与回应去年的文章吧。按前文所说,那是一篇喜大于忧的文章,这意味着许多问题在那时已经得到解决或者看到曙光,以至于(当时看来)未来的生活相对比较轻松,不太会有个人历史的包袱。这一年过得也的确如此,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我能平稳应对频繁到来的版本迭代。
看到前文对容器论的论述,才意识到一年已经过去了。我时常有意无意地在想,现在的我还属于第三容器吗?或者说,我需要抛弃第三容器创建第四容器吗?一个直接的回答当然是不必要,因为新容器的创建本身便是逃避,以求无压力无负担地重头开始。而这一年的历练一方面让我意识到,我还有余力应对,另一方面更让我意识到,我或许已经无处可逃了。
这或许是一种更高层面的悲观。曾经我可以通过生活环境、人生阶段的调整,自然而然地创建新的容器而主动摒弃过去的联系,如今世界(至少是中美欧的世界)在我心目中已然连为一体,三年的病毒大流行也造成了种种虚幻理想的破灭。曾经的我或许认为世上还有理想乡,如今的我只能将理想乡在心中建构。
不得不提,九年前在图书馆读《三体》时的震撼影响至今。一方面,它让我燃起对物理的兴趣,趟了一条纯物理-数学物理-物理理论应用于数学的学术之路。另一方面,它对我三观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曾经我感叹于书中广义人类的可笑与可悲,对主要角色从共情转向迷茫,敬佩而不知所措。如今更可悲是,这世界上的人类比书中更为不堪。只能进一步感叹小说来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甚至美化了生活。曾经对着哥谭市的蝙蝠侠讨论正义性,见识真正的地上哥谭后发现与我无关的地方不配被我谈及正义。
这是否是某种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或者更深层次的迷惘呢?或许是,但好在这一场合早已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比对和探讨中处理过了。前文提到,第一容器中“由于校园经验的单一性,思考大多处于假设阶段,在实践层面较为生疏”,如今走出校园,过往的思考则能化为思想的武器或盾牌,避免我向深渊跌落。我无需而又无法创造第四容器去逃避,只能或必然要直面眼前纷乱的世界。
第二容器的障碍,我在过去一年数次梳理与尝试从不同的角度面对与解决。我想我还未完全成功,但实际上已经剥离出了其间最核心的一点。那便是,我意识到自己能力已经不再能够毫无保留地为他人(家人、朋友、同事、陌生人)运用了,反过来即是第三容器的核心“指向自我”。这是一种退守,认清自己并非无所不能而选择优先成就自我。这种自私是我心中最大的心结,因为它意味着我对过往自己背叛的第一步,而极有可能一步一步让我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解放出原先用于成就他人的精力后,我确实在攫取事业发展契机中更上一层楼,用流行的话说就是成为卷王。而可悲的是,我意识到在不公平的竞争秩序中,我需要至少高出一个数量级的成就,才能获得应有的对待。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小镇做题家心态,只是这里的“小镇”并非字面意义,而是我的家庭、国籍、种族、身份、个人经历等一系列事物。
我对这种现状感到愤慨吗?似乎是而又似乎不是。从小到大,当我面对强加的苦难时(以高三与军训为例),会选择摸清苦难的规则,在框架中尽情偷懒与飞舞。另一方面,我又永远不会感谢这些苦难,而是希望后来人能够避开它们,如果依旧不能,那便传授些偷懒的技巧。这种态度建立在祛魅之上,因为我意识到这种强加的苦难不过是社会的某种驯化。有些驯化我乐于接受,那便享受其中,对于另一些驯化,我最喜欢的词依旧是“阳奉阴违”。
可笑的是,我曾经还为海的那边幻想了不存在的自由。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驯化罢了,尤其是在各个国家待过之后,各处不同的嘴脸便暴露无遗。祛魅之后,面对驯化便无需恭恭敬敬,而只需用“微操”谋取最大的利益。更滑稽的是,当我意识到一切的规章制度都不过是制定者谋求合理性的一种手段,那么结局就是在最低限度地符合之上,直面背后制定者的需求。
自私的人是没有弱点的,而我不想成为自私的人。我一次次返回到第二容器的最终问题,便是希望在自己事业按预想道路前进的同时,重新分出余力构建与他人共同的优秀生活。年初到出国前,我在事业道路较为轻松时,确实又一次做到了。这给我很大的鼓舞,甚至会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心不息的力量源泉。而出国后,亦即回到第二容器最终问题展现的环境,我依旧未能成功,或者说,曾经我注重与他人的联结而造成个人事业的苦难,如今我便选择了优先应对事业。这是对自我能力不足的一种再度确认,这一次似乎却让我更为平复地接受。一大重要的原因便是上述心中的力量源泉吧。
然而近来世界的形势,却让我站在再次跌落的悬崖边。具体而言,我需要再度抉择保全自己或是兼顾他人。过往的生活,让我已对海外的陌生人丧失了共情,对同事也只能报以毫无根基的相信与祝福。对于家人、朋友、还有19年在我迷茫时刻给予我力量的广大身边的陌生人,内心的声音告诉我,似乎我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而现实却又告诉我,我的能力不足以为他们做什么,时代的苦难无差别地落在每个人的身上时,或许最终只能靠每一个自我去面对与消化。这两个声音是两个极限状态,而生活则介于两者之间,且有无数的随机性和环环相扣的境遇。我只能预见未来的不确定性,却无从知晓这不确定性最终会指向哪里。
一直以来,我总假想最悲观的场景并为此做(心理)准备,这样事件实际发生时,或许总还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目前我心中有数个最糟糕的情形,就不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了。冷酷的理性告诉我,人生一世,最终一切都要离去,不过是在什么节点罢了。提早看淡些事物,明确各个要素在心中被放弃的排序,紧抓着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也预先告诉自己某一时刻需要彻底放手。在此之上,或许在身边人看来,我反倒是最乐观的那个。我心中不断浮现“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场景,说不定,我真的要在未来一年的某一时刻,对着纷乱的世界放声歌唱。
最后简短地提及未来一年的能落定的计划吧。过往一年,自《纯粹理性批判》起,至《存在与时间》止,我的哲学史观已从文艺复兴(以笛卡尔为代表)迈入了前现代。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便是自萨特、加缪起,至齐泽克、巴迪欧的现代哲学了。原先曾翻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加缪的《局外人》,但当时的情境并不合适进一步深入,希望未来一年能有机会走完这段哲学之旅吧。那一时刻,或许是我七年前许下宏愿“通晓数学、物理、哲学”完成之时。
10:29 2022年12月11日
在悬崖边张望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