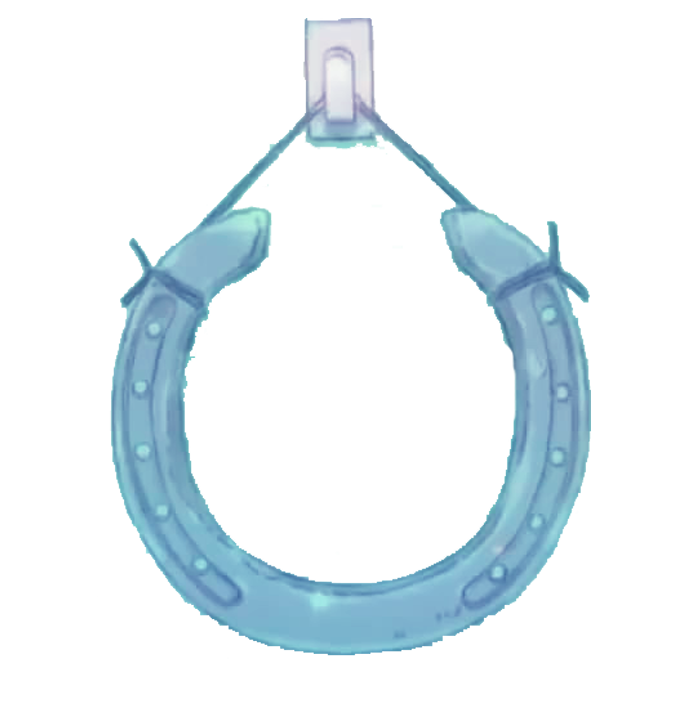他人与折磨
自十日谈后,我已彻底重新倒向了为他人的存在,为己的部分只用于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为未来抽象他人做准备。这算是某种复活与回归本心,然而我也需要重新应对他人带来的折磨,甚至进一步地,自己给他人带来的折磨。
现阶段的主旋律当然是尝试内化与超越《存在与虚无》,萨特在他的另一部剧本中提到“他人即地狱”,而在此书中也仔细剖析了他人对自我的影响状态。抽象层面的处境即自由地相互干渉除非互相物化,我早已了解,此文更多的从个人体会角度出发,尝试在“术”的层面给出一些解法吧。
首先,我深刻认同与他人的共在包含在此在的本质属性里,我曾经的指向自己不过是将目之所及的他人(包括朋友与家人)全体物化已达成我眼前的实际目的罢了。在我目之所及之外,他人自身仍在以一种我不可控的方式演化。而当具体目的消解、物化淡去时,演化后的境遇已与过往向我偏好的方向迈了一大步,尤其在开诚布公与复盘的角度,让我对以往的经验有了相对更全面的认识,这也让我足以认可重拾过往心态的必要性。“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让我从鄙夷到接受到再次反对,因为我并不认可命运的存在,包括他人的命运。况且随着身边他人的成长,我已能从中摄取我无力涉及的点,拯救他人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拯救自己。所以对我而言这句话说两遍就可以自我取消。不过对我而言,在这句话中,我尊重命运的“他人”是对我而言无关紧要的人,对于那些对我而言重要甚至处于亲密关系的人,我的存在本身便是Ta“命运”的一部分,我做任何事理论上都是在尊重Ta的命运。
所以在与他人关系的两端已有明确安置:曾接触并无意进一步发展的“他人”尊重其命运,对重要与亲近的人积极地创造改变“命运”的时刻,当然同时对还未接触的迷雾中的人抱有开放的兴趣,所以这个体系里对我而言地位最低的,便是熟悉的陌生人。然而哪些人是熟悉的陌生人,哪些人是因为没有合适机会还没进一步接触的人,我心中似乎有杆秤,那边是折磨感。
如果与某人的接触已让我感到时刻在消耗能量,能量至最低水平时也无法开启省电模式时,便是折磨时刻开始时。若是短暂分离使我能从别的活动或接触中获得能量,或许还能重新友好的接触,若是这折磨时刻始终持续,那或许甚至会从不主动见的人变成不想见的人。第二容器的末尾便是遭受了一系列折磨关系,使友情和心力耗尽,我直到在新的接触中获得巨大能量后,才能重新尝试接触,不过仍旧以折磨终结,于是便就此封存。当时的灵魂拷问“我是否只和与我相近的人接触”我无法彻底反驳,但至少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对自己说不需要和折磨自己甚至互相折磨的人继续接触。
那么折磨的来源是什么呢?人们互相接触而非过一个人(物化其他所有人)的生活,必是有社交的需求,那么社交的需求除了杀时间、情感寄托(被用烂的“情绪价值”这个词),恐怕是对不确定性的向往与好奇。这种态度在未接触时会促使其诞生,但在诞生的瞬间便会消失,剩下则是一片全新的“竞技场”。当然我并不希望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接触描绘地这么有攻击性,或者用“创作场”来描述更为贴切。即每次接触都创造出一处“话语”或“交流”的空间,需要双方或各方通过各种言语或者行动去充满。光芒四射的人当然能预先为这一空间铺设好水电网气暖,让加入的人们舒适地展现,我曾向往这样的能力,却在向其努力之后意识到这并不值得成为理想状态,除了需要克服的费力,还有逻辑上绕不过去的刻意,更有加入的人们毫无察觉带来的进展的停滞,甚至导向我曾关注到的因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公平导致另一方对这一方的不平等的问题。于是我如今倾向于锻炼后却并不时刻施展这样的能力,一来在效率和心力层面有所节省,二来在呼吸困难时吹来春风比上来打开空调更为舒适。
不过这又要让我警惕囚徒困境,即我本人向往协同铺设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与不确定性带来的惊喜,而我若总是伺机而动,那么结果便是所有抱有我这般想法的人都无法达成目的,这一点上我倒是秉持着康德的道德假设,即接受世界上所有人都如此做后的境遇后才决定做某件事。所以场面便又演变成了我先抛橄榄枝,如果对方有所回馈后便再度掏出更丰盛的活动与主动的态度,以此来回向前,像是找到能力相当的乒乓球手才互相打上几个球。
近来的些许事件让我在这一模型上又决定进一步修正:能力相当的乒乓球手本就不多,如此迂回向前在时间充裕时效果尚可,在惊鸿一瞥之时或许会错失良机。而出手便是全力一来折磨自己,二来又会让对方惊诧而无所适从,若恰好没有动力对抗便也会陷入折磨。另一方面,当在场人数即处于对话中的人数上升时,情况还会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在场的人与我是不同阶段与状态的朋友时更是如此,我也时常会在这种场合下倒向“自然状态”,即放弃对对话整体的思考而沉浸在对话之中话到哪儿算哪儿。然而事后却又认识到似乎本有更合适的方式,只是当时上头了就想不了那么多了。我将其称之为N体问题。历年来的交流经验让我对二体问题有了充足的经验,虽然仍需提升,但我至少基本能达成我想要的环境与结局,至少能不留遗憾。而近来时常经历几组三体问题,而且是三人都互相在不同角度熟悉的境遇,一来让我明确感受到即使如此也与二体问题有所差别,这是应了萨特的话,两个人的共同自由即使存在也会因为第三个人的在场而消散。二来我会觉得理性讨论的话三个人是合适的人数,因为两人对话时剩下一人便有空思考,话语的空间也无需时刻发力占满,当然两人时便需要引入沉默这尊大神。不过近来涉足四体问题时便透露出了算力不足的状况,更何况著名moba游戏们都是五人,等我哪天搞明白如何应对五体问题或许才是大成。
提到沉默,不得不说它从曾经我担忧的对象变成了我尝试用顺手的工具。沉默可以用于节能,可以用于反抗,也可以用于间奏。折磨时刻的诞生往往源于所处环境已无法让我实现想法,而我又因为时间或情绪的影响而希望在这一时刻继续努力,因为成功往往也是诞生于挣扎与钻牛角尖中。但如今若非遇到本质诉求,我便选择使用沉默,不想解释也不必解释了。不过一般此招一出,我就已经能坦然面对“没有过往激情”的质问,因为我的激情已有了别的输出口。
总体而言,当我身边没有朋友时,我会更为主动地与人接触,遭受折磨也安慰自己只是失败地尝试,而我身边有朋友时,我却还要暂时忽视他们的存在,让新出现的角色有展现的机会,而又不堕入喜新厌旧的心态,真是着实困难。当然我如此脑回路中最大地值得批驳的点,便是我用某些游戏抽角色的心态在玩真人社交,即使告诫自己不要物化他人,又可能陷入描绘他人故事或理解他人也只是与角色背景故事共情的境遇。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得回归萨特那儿在抽象层面的讨论,对于这篇务实的文章而言,所有“他人”可能都被简化为三次元纸片人了。
15:47 2023年10月22日
担心被再度折磨而又逼自己勇敢创造机会的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