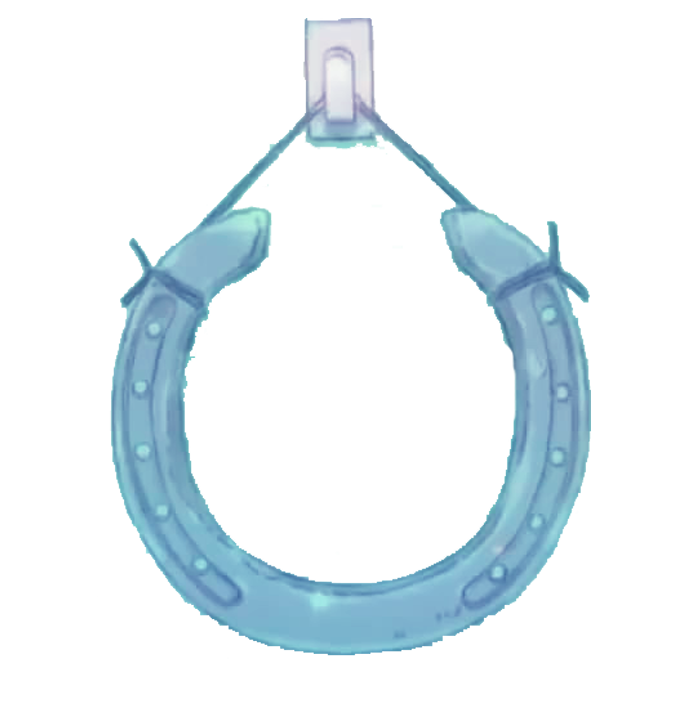异类与联结
朋友说我喜欢跟一些人在一起是因为归属感,而拎起了“对他人评价是自我映照”的锤子的我下意识地敲了一下这个钉子,反过来想,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能否用更准确地表述呢?
我以人类学这另一模糊地表述代替我心中所愿,是因为人类学著作描绘的若干感受与我有所对照,其重要的一点(主要来自于《天真的人类学家》)便是来到新的群体时表现的像异类,遭受各种文化冲击,而当拙劣地逐渐适应与接受这个群体时,再回到过往的群体时又成了一个异类。而新群体中的所谓适应,也不过是尝试着站在原住民角度上理解文化共识。人类学家或许享受这种异类到融入,甚至在各类文化环境中跳转的感受,而我在关注人类学初期时便明白我的最终落脚点并不在于此,正如研究了解哲学不是为了成为哲学家一般。
于是又转向那个经典问题“认识你自己”,于我而言这一名言需要转化成“创造我自己”,因为认识指向的过往自己不自觉下显露出的表现与倾向,而创造指向的是还未成为现实的潜在的自己的可能性。我曾不断地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用半年的时间关注与探索了过往(尤其是十年前)的我关注的答案即亲密关系,发觉过往的我所能幻想的最深入的关系,如今看来并不困难便能实现,而过往的我称之为理想的一个点,如今也进一步展开出更高维度的复杂性,让我在实现了一部分后仍愿意在保留这部分时更进一步。这或许也是理想得以实现的最佳形态了,一步步走向目之所及的部分,享受移步后带来的新乐趣却又不停留在一处直到厌烦。
理论与现实的分界线的问题在此刻对我又有了新的切入点,现实意味着确定而无法改变的状态,犹如物理实验中测得的数据,没有任何原因,发生了就是发生了,而理论可以尝试对现实展开解释,用以试图预测未来的现实,也可以构建一套本不存在的新说法影响现实。偏好理论则是相信现实的可塑性,偏好现实则是将一些已有的现象与说法当作既定事实。某个具体的事物(如我正在乘坐的飞机)在出现前不可想象,却在实用后被接受而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我自己也不过站在了理论与现实光谱中靠近理论的那一侧,追求现实的语境下我会成为异类,追求纯粹理论的语境下我同样会成为异类。
或许有人享受成为异类,常见的句式便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我却寻求异类间的联结。讽刺的是,“常人”的模样大多相似,而异类之间却各有不同,本就拥抱了随机空间,却还希望在随机中恰巧遇到一个相近的人,这被称之为“缘分”,而我又相信随机带来的在地性的脆弱,主动选择才更凸显偏好。或许这也只是现阶段的所谓理想视界所能达到的极限,仿佛爱在三部曲第一部邂逅后失约带来的八年失散,我已不相信随机的邂逅,而在意主动后的赴约。
可惜如另一个朋友所说“老朋友不是一开始就成为老朋友的”,与朋友的联结始终要从陌生时的初识开始,有实践经验后,所能做的只是加快这一进程,当然还要背负拔苗助长和不“顺其自然”的诟病,不过于我而言,探索交往的节奏本就是我的兴趣点与“自然”。我不肯屈从“常人”的言语的一大原因便是,随意听信只会让潜在的那个人失望。这次北京之旅最让我留恋的话或许便是“两个人一起喝醉,难受的也只有自己”,如同南美之行“标准是给不爱的人准备的”一般,会不断地在我未来的抉择中展现出来,轻巧的大道理确实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认可后坚定的实践直到新的强力回应的出现,恐怕是我最成为异类的点。适当地学习了迂回与拉扯的原理后,我还是发觉真诚的主动出击才是导向我所偏好的联结的重要方式。
数学作为事业越发退居二线,而副线的稳定与不强求,甚至有章可循到可以预期,或许才是它在我心中应处的位置。于是让我在寒假剩余的三分之二时间,再度探究旅居与数学灵感的联系吧。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只能先只身在江湖游荡了。
13:37 2023年12月24日
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