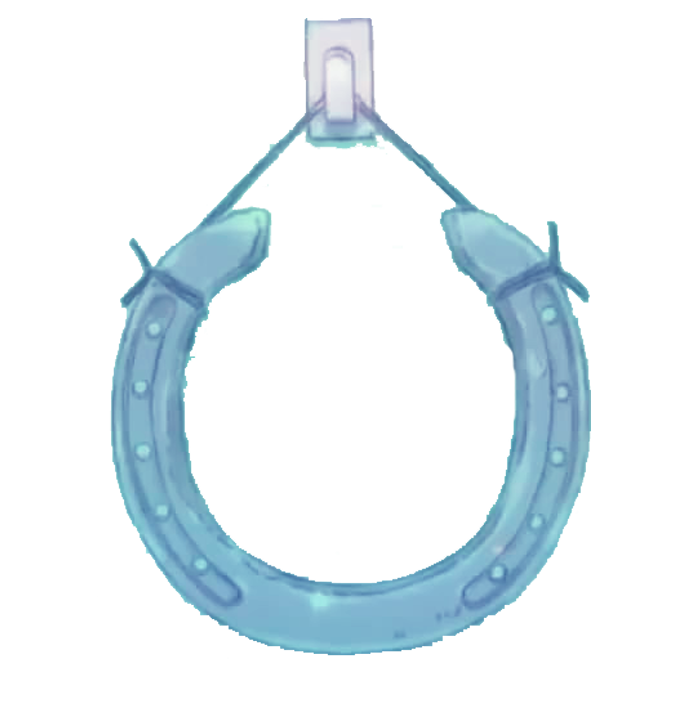从哲学到人类学
欢迎再次来到年更的生日文,这回要一并挑战与回应过往的七篇生日文(2015,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因为我的问题列表已经追溯到了十年前的2013,当我遇到哲学前的时光。那时探索(或者直接感受到)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爱的追寻。哲学的旅途让我对理性的能力与范围有了明晰的了解,而探索爱,除了《存在与虚无》 中文字的答案“给他人自由,又希望他人自由的选择自己”,还需要像理解《存在与时间》 那样在生活中实践。人类学,或者我自己定义下的“探索人何以为人”的人类学,或许可以代替哲学成为下个阶段理论与实践的统称。
上述的七篇生日文中,恰巧缺失了2016年,而那一年正是“要把生日这一天纯粹奉献给当下的自己”这一想法的首次实践。简单解释一下,曾经的生日希望与朋友共度一小段时光,也希望借此做个人的总结与对未来的展望,然而前者关注了当下的他人,后者关注了过去与未来的自己,“当下的自己”指的是正在过生日这一天的自己。从反方面来说,我并不想在这一天也为未来和过去的自己打工,而把每一天的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其中生日这一天的自己是纯粹自由的,我只关注这一天0点到24点自己的感受与愿望并加以实现,而不必谋划未来。虽说如此,如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有回溯过去的意思,早上起来也回了一封房东的邮件,也相当于为未来回到波士顿的自己打了份几分钟的短工。严格地关注当下的自己,首先需要隔绝手机及社交媒体,直面自己当下的愿望去实现,这点在2016年确实是实现了,以至于我生日次日回到寝室时才意识到我收到了几份改变我与朋友关系的重要礼物,但那已是第二天了。昨天的我还为今天的我打了份工,埋下了一些伏笔,再加上今早拉开窗帘便遇到了北京送我的第一场雪,希望今天也能实现“当下自我”的愿望。
过往生日文的总体画风是回应过去的自我提出的问题,看是否解决,再向未来的自我抛出问题,关于爱或者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是在暑假时翻出十年前的日记时重现的,仿佛是收到了过去的自我寄来的信,拷打久未面对而又恰好余力地当下的我去重新探索,反倒像是一份给当下的我的意义的礼物。日记中让我感触最为深的是清楚地记下了最终抛下爱的问题转向数学的世界的时刻(与此同时应该也遇见了哲学),当时的不舍与遗憾,借着文字还能让当下的我感同身受,我无法跨越时空抚慰过去的自我,但我可以让未来的自我想起这一过去的自我时也想到试图抚慰过去的自我的当下的自我,这是我自此之后许多行为的出发点。
类似的,2015年后的自我也有许多新的问题与遗憾,表面能对外人道的部分在生日文里记录下来,那些隐秘的部分或许只能通过回忆或者其余时间的博文片段中解码出来,也有可能就此遗失了,人生也是要接受遗憾的存在的,但与此同时也要不放弃解决问题的努力。当下的我粗略的感受是能够想到的15年后积攒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像是当年的生日文里提到的高中问题列表一样(与优秀的人的比较时自己所处的位置、与一般同学之间的心墙、患得患失的只伤不悲、玩伴和挚友之间之间的转换、外在要求和内心想法的冲突、选择未来方向的方式、希望得到关注与承认的状态、学业与课余的交织、对爱与友情的思考、与社会之浊的对抗、生活孤独的体验、对自己生活应有的态度等等),但实际上有些终极问题又会在未来以新的形态重新冒出来,所谓解决只是一个让当时的自我看到或所想到已能满意的答案。
让我来从过往的生日文中拙劣地解读出过往的期望吧,15年的短时期望是看完列举的书与迈出知识范围的小圈子,而长远的愿望则是感受世界的缤纷与拥有更强大的内心去平坦面对精神的猛虎。短时期望往往在一年内便已完成,而长远的更为抽象的期望则没有一个明确的完成标准,只有每一时刻是否满意。此处感受世界缤纷的愿望成为了此后容器论中第一容器的主旋律,虽然至今容器论也已经被我舍弃了。这一愿望如今也从主线成为了副线。
16年没有生日文,但当时的愿望在当时已经提到,即让生日这一天为当下的自我而过,那一年的生日我没有和任何人说,搭着公交和黑车去了没什么人的金山岭长城,从滑道上一路溜下,然后花了当时的重金去了私汤泡澡,一个人看了一部宫崎骏的幽灵公主。而长远的期望则是能有人能与我或为我共度我的生日,不至于“连一起逛未名湖的人”都找不到。实际上今年的生日也有部分为这两个期望还愿的因素,也算另一种意义上的为过去的自我打工吧,但因为当下的自我的期望的一部分就是为过去的自我打工,所以“还愿”的活动被在行动的初始便被赋予当下与过去两重含义,实际上往往又会为未来埋下伏笔,如此丝丝缕缕的联系倒是被我津津乐道,并由此编织出自我叙述与意义感的大网。
2017年的短期期待是让未来的交换生活成为那时当下各种问题的破局之法,长期期待是面对或解决沉沦的必然性。如今回望,出去交换的瞬间被我认为是第一容器的结束与第二容器的开始,而事实上第二容器在物理层面上实现了对世界缤纷的探索,而那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挚友的存在性,在交换的过程中变得更为凸显,因为异国他乡的环境让我必须时刻直面自己。这一点上的挫败也成为了第二容器的终结点。沉沦的必然性也是困扰了我五年的问题,在博士毕业的暑假重读《存在与时间》时终于在行动上理解如何应对,却又在博后第一年的末尾一度再次陷入。但第二回只花了几个月便再度走出来了,所以如今到不甚在意这些,只是发觉与朋友们的探讨中许多的挣扎点来自于此,而我的共情反而变弱了因为我不再担忧这个问题,所以作为副线还是有调整的空间的。
2018年时已经有明确的回应过往问题的倾向了,我总结起来倒是方便了不少。“一年前我手头剩余的open questions有:沉沦的必然性、旧环境的破局、挚友的存在性、个人随想的接续。喜人的是,除了第一点,后三项都在这一年中成功且圆满的解决。”,我在写下上一段文字前并没有发觉这段归纳,不过至少蒙中了三个,因为个人随想的接续(或者务虚)在近来的状态中充裕到满溢了所以被我忽视了,但那时堕入务实而不再反思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此后“指向自我”的第三容器中又经历了一回并花了更久的时间和更多朋友的助力才让我再次“醒来”。破局确实成功了,存在性也确实保证了,但生活是向前发展的,过往带来破局的波士顿反倒如今成了困住我的局,我在挣扎了三个学期后仍旧没有找到破解之法,并且对容器论的抛弃让我无法单纯逃避到另一个地方(比如目前所在的北京)来解决,而必须督促自己在另一个地方补充能量后在新的学期再次挑战,否则我根本毫无理由待在波士顿(其实一个核心的理由是为了钱,但这不应成为本质理由)。坚定对人类学探索的想法为下学期带来了些许期待,我大致筛选了哈佛人类学系的课程,希望借此了解人类学的方法,也由此拓展新的社交圈,这算是顺便一提的当下的短期期望了。
挚友光有存在性确实不至于让我满意,但至少让我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去探索,用一个数学的比喻来说,如果加了一堆条件研究半天是个空集那么就没太有意思了。此后随着探索的深入(当然有反复与挣扎),如今已经迈向了对亲密关系的探索,挚友这个词也已经进入到了历史文献中了。近来在利马的感受也让我对爱的存在性得到了“证明”,所以亲密关系与爱终于让自己成为了值得探讨的话题,这也是人类学探索之所以有可能的一大前提。经过哲学的历练,我并非希望搬弄一些我自己都不理解的词汇,而是希望知行合一,将每个词至少赋予我自己的实际经验层面上的含义,虽然进展到能为外人道也,则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就像我自己在实践层面解决了沉沦的必然性的问题,但希望将此传达给我因此而挣扎的朋友们,光靠理论和语言的表述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具体的事件与实践来尝试与引导。不过与此同时某位好友祭出“虚妄”的大招,即尝试总有失败的可能性,避免失败而不如不尝试,我暂时无法反驳,但还是先头铁地用行动去判断。
当我仔细阅读18年的生日文时,发现确实又预判了当年的问题,由此又获得了自我同一性的例证,当时最大的长期问题是情感的实践,其现状便是上文对亲密关系与爱的探讨。另一方面,当时的短期问题是阅读的重建与学术的起步,后面我用事业代替了学术,但现在一想这只是第三容器时的情况,如今的人类学不仅代替了哲学作为方法论,还代替了数学成为了我新的核心事业,即(这一阶段下)愿意为此投入无穷的时间、精力,可能还要加上感情的活动。数学自此退居第二,倒让我放松了一口气,因为当它不是最终或者最核心的事业时,我不必时刻以它来为自己赋予意义,反倒能对此更有平常心,据我的理解这或许才更能通向数学前辈们理想的道路,而非死磕型不死不休的奋力挣扎。以及我在数学合作中再度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与维护的重要性,否则便又是萨特口中的“他人及地狱”,所以实际上即是是为了数学的前进,也需要人类学的探索。实际上这一转向在暑假末便已发生,只是如今我在离开波士顿的前几个小时终于领悟到人类学这个名词而已。念出名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彻底地转向,因为名字只是个代号,其后对应的是无穷维的空间,而没有名字前只是将标签作为代号,其对应的是有限维的空间。有限对应物化,更高的维度只是尝试更丰富的展现,而以有限暗示无限才是我追寻的方向,叫出名字是重要的第一步。
阅读的重建,在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三大批判的启动后已不再是重大的问题,我也通过学术的实践学会了带着问题去阅读,书籍反倒从指点前方的明灯变成了参考文献,这一对书籍态度的变化,被我解释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整合的结合。在数学和哲学上,我都曾有段时间陷入过思而不学则殆的困境,如今思学结合,书籍反倒也成为了一个副线了。从前文至今,我已经提了许多曾经作为主线而如今变为副线的活动,其实恰巧是过往三个容器的核心问题即探索世界、结交挚友、事业发展,它们在我心目中仍旧重要,只是不再占据第一位置即主线了,如今的主线是人类学或者说亲密关系或者说爱。当时的事业狭义指的是数学,但如今我甚至可以把物理、哲学和对应的书籍阅读、课程了解都归为知识积累层面上的事业,前段时间我曾感慨走完哲学史后不知走向何方,也考虑过看《资本论》往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走,但拷问自我后,我发觉个人如今的核心兴趣还是探讨个人的生活而非大词构建下的叙事,我甚至不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思考以故事或小说的方式呈现,因为我觉得形成这种故事性的叙述便必然考虑到读者或艺术性的感受而裁剪材料,而我希望直面生活。学科分类下的人类学当然是无法满足我的,因为我既不想搞研究大猩猩的人种学,对深入部落总结文化发展也兴趣索然,正如我学哲学不是为了成为哲学史家或哲学职业者而是为了个人的哲学思考,我了解或者学习人类学也是希望学得人类学看待事物的方法,而非投身于人类学的职业。近来火热的人类学家项飚有本《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访谈,我对标题深以为然,却对内容兴致没那么强,一来可能我没有进入人类学的语境,二来我关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根本就不是官方人类学的关注点。但于我而言官方不过是陈规罢了,借用近来偷学的观点“标准是给不喜欢的人准备的”,我可以理解成官方的陈规不过是对过往创新的总结,而创新本身就不是被总结出来的。
上述岔开来写了一大堆,点开19年的生日文发现又莫名其妙押题成功了,当时的长期期望恰好是理解理论与现实的问题,并且还恰巧是看《资本论》开头时引发的思考,这倒是给我重看资本论多了一个助力。对于理论与现实,其实核心问题倒不是选择哪一个,而是什么是理论什么又是现实,我上述说了一大通只能表明我的偏好,如今问我这个问题,我似乎还是一下子答不上来,那看来我还是发现了一个遗留未被解答的问题。但如今我还是有更多的理解的,或者仅仅是更多有趣的发现,原先我以为是理论的物理、哲学、人类学似乎有着指向现实的情形,而原先以为是现实的所谓应对现实世界带来的压力的(往往来自于朋友的口中),反倒有点像朴素的理论总结或定论。这又让我想到近来与朋友达成共识的两点,一是人是复杂而发展的,二是要爱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关于后者我还从某乎看到个观点,爱抽象的人比具体的人更简单,这实际上呼应了第一点。过往我对理论的偏好或许可以被解释成类似真空中的球形鸡的简单情形,而当我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时,我也并不希望如上文人类学家那般直接投身田野获得第一手资料,而是希望在理论上明白后再稍微多走一步将其应用到实践,这实际上仍旧是理论的活动范围,只是素材中有更多现实的“事件”被纳入了考量。关于“事件”我多提一句,巴迪欧有一本《存在与事件》,原先我以为能像《存在与时间》和《存在与虚无》一样成为改变我的存在三部曲之一,但他用集合论的想法去搞哲学让我先天产生了一些偏见,最终留下来的只有“事件”本身与事后的解读同等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都不出自于他,而只是“事件”这个词给我带来的联想,就像《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样,最精妙的叙述是这个标题。或许未来我也可以写一本《存在与xx》来当作时间、虚无的精神续作(这倒是可以当做长期期望),我想填个爱情,却又觉得这个词不如爱来的有力与宽泛,所以暂且留着另一个字吧。
2020年的写作生日文时陷入深度的务实的沉睡,反倒在理论与现实中选择了前者,并尝试做了辨清“如果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理解它们,并将它们作为应对世界运行的一种工具,是不足以满足我的”,我指出了“关注内在的需要而非外在的表象”,“凭借心中的愿景和冲动做出行动”,“保持原始的好奇心,而不仅仅跟在别人后面”作为对未来的长期期望,如今回忆起会觉得这是当时沉睡时能想起的最为“务虚”的说法,毕竟前一年的短期期望是完成第一篇论文,而这一年的想法也是尽可能多的完成论文。这一点恰巧呼应当下的又一短期目标即“独立”完成一篇新的论文,作为初段少年迈入二段少年(或者三段)的标志,这一点也是近来痛定思痛终于下决心摒弃合作的舒适区得出的决定,背后有许多务实或务虚的话可以谈,但在此便不多说了,因为有些偏离大主题。而上述三条对务虚倾向的表述,如今则是确实在做的,我盲猜下一年的生日文回应这一点时感到自信终于可以重拾务虚,如今的我也确实仰仗当时在务虚与务实间坚定务虚的我,在这种意义上选择理论而非现实,可能与如今对理论与现实的理解略有偏差,正如上文所言,问题不在于我选择哪一边,这其实是明确的,问题在于我用什么词去称呼它们,不合适的词反倒会导致我声称面对现实实际上只是玩自己的理论框架的滑稽,所以对理论与现实关系或界限的理解,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021年的生日文提出的问题是解决第二容器以及调和科研与阅读哲学著作两件“真正想做的事”之间的冲突。前者已然解决,或者至少迈入了新的话题领域“亲密关系”,后者上文也已提及,比较有趣的点反倒是科研、阅读、哲学都已经成为了副线,而“真正想做的事”被改变了。当然这一年很大一段时间我在拷问自己什么是“真正想做的事”,所以也只是将将解决,未来也会作为副线不断地被短暂回溯。当年最大的收获是遇见了康德,使得对理性本质的了解成为了可能,我的个人思考模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刷新。
2022年深处疫情放开下的隔离状态,看成最为魔幻而又现实的一次生日,以至于今年我不仅想还16年的愿,还想还上上一年的愿,包括还愿的说法都是23年初希望再度来到理想之城桂林时的说法,好在桂林没有辜负我的心愿,圆了过去的回忆时还增添了新的美好回忆,由此影响了一连串的未来。
这一年的短期期望是完成后现代哲学的阅读,借此实现八年前的宏愿“通晓数学、物理、哲学”,这点确实做到了,并在人类学这个词出现前还给我带来了些许迷茫,即梦想实现后便不再是梦想了。而长期期望则是探明再度面临抉择保全自己或是兼顾他人时刻自己真实的心意,当下瞬间的我经历这几个月的纠结,还是会选择兼顾他人的,然而这个问题自《三体》中对罗辑、章北海与程心等人的塑造便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至今记得对程心威慑失败后为了“爱”丢掉发射器时的认同和此后情节展开时的不知所措。不过阅读三体恰巧在13年对数学的转向前,所以再次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归结于十年前的问题而不必当下便给出答案。
于是简单概括,当下的短期期望是在一是某一时刻读完资本论,二是了解人类学的思考模式,三是了解诗歌与诗人的感受,四是完成新一篇独立的论文;长期期望一是对理论与现实的划分有明确的表述,二是对亲密关系与爱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具体而言我终于明白了爱的感觉或诞生的条件(之一),但仍对爱的发展、转变、消失等环节以及最终能拥有的可能性抱有疑问,三是在面对爱的同时也进一步尝试解决家庭的关系,这实际是对爱的问题的一个分支或者应用,不过牵扯经济和更多地个人历史,所以会更为困难,我暂时预计至少需要两年。最后是找到更多“真正想做的事”,不仅是解决过往年少时无法面对的遗憾,还要让当下的生活凝练出新的观察世界、人类、自我的角度,否则便会陷入“用一生治愈童年”的流俗说法。虽然年少时的遗憾背后或许本身就是一个个能够探究终身的终极问题,但我正如我上述许多的主线演变成副线,终极问题也可以在某一阶段集中面对而在此后的阶段成为副线,这已经相当于某种变相的解决。
用这么长的文字来回顾过往的生日文并阐明十年前转向前的问题,我想也需要提几句进来已经有许多描述与讨论的额外的问题,这些都是潜在发展成新的“真正想做的事”的契机。自上次生日文后接触隔离,我实现了许多过往的梦想,也找了打开许多过往纠结的钥匙,它们甚至是交织着向前进的。随意列举一些,流水席的出行为挚友问题找到了完美的解答,又在淡如水与江湖再见的语境下被反复回溯;理想乡桂林与异世界南美的还愿之旅生发出意外的探讨,让自发明的Question代替Queer占据了LGBTQ的位置,也让问题从性别性向还有mbti式的人格认同转向了对身份认同与标签认知本身的思考;潮汕与国庆节对虚无与爱情的十日谈,转而又面对荒谬与虚妄,痛苦与折磨,让一个个大词在探讨中有了实感;暑假在欧洲对理想乡与“真正想做的事”的探寻,如本科毕业时全国旅行版高强度祛魅,却已不再又过往探索的激动,反倒是在学术与生活的结合中让我找到了幸福生活的秘诀,进而完成了学术品味的建构与实践,在三定律“幸福生活、凝聚数学的motive,玉碎数学”中保留前两个而最终以人类学的方式背弃了数学,还得背弃人类多样性观察。客观来讲,这一年的版本更新非常频繁,已经从二十一天定律变为十天定律,实际上会让过往的我激动兴奋,却让体验过真切幸福感、虚无感与爱的感受的我觉得还不太够,只能说阈值在不断提高,近来甚至破除了性、烟、酒等常规放纵手段的诱惑,因为我发觉(或者未体验过时的认为)这些事物能给我带来的刺激远没有过往体验到的那些感受来得强烈,所以我还是贯彻喝白水说醉话、嚼巧克力棒当叼烟、性作为爱的辅助与工具的方式,为常规的解压方式安排一个奇妙而滑稽的位置。
要不此次的生日文还是点到位置吧,回望过去展望未来,哪有面对当下来得真切呢?生日过去了12个小时,剩下12个小时就纯粹交给今天的我吧。
11:52 2023年12月11日
衣服